《不恋爱的两人》剧情介绍
——不恋爱就不会幸福吗? 未曾喜欢别人、不知人为何接吻、困惑于不懂恋爱与性的女性,邂逅不想恋爱、对性亦无兴趣的男性。 情侣……夫妻……家人……皆不算?两位无浪漫情结无性恋者(aromantic asexual)开启的同居生活,在父母、上司、前男友和邻居中掀起轩然大波…… 屏除恋爱与性的二人,关系将何去何从?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求婚大作战黑帮大佬和平梦致敬英雄战境:火线突围英雄与懦夫日照重庆海边的恋人们夏威夷之恋邪神女巫会旧伤人兽杂交无籍者七宗罪纵情一曲七号房的礼物C.H.U.E.C.O.我们死去的那个夏天10·豪快者间谍过家家第二季功夫乐翻天记忆禁足少女罗曼史蜜桃女孩联邦调查局:通缉要犯第四季搏击人生伪恋OAD:丢失/巫女小姐灵媒缉凶第四季呆瓜兄弟法兰西特派骄阳似火
《不恋爱的两人》长篇影评
1 ) 如果你也曾经写诗
我们挣扎的青春挣扎的人生挣扎的人格与信仰物质和精神化成鸡蛋和诗人 就这么单纯盗版光盘能否买来思想当诗人去卖鸡蛋 当诗人写的不再是诗你早就不应该养鸡了为什么呀养鸡多傻呀那你早就不应该写诗了为什么呀写诗多傻呀你是我的颜色我为你调色而你却终于无法分解成红黄蓝方方走了我再也不想写诗了我再也不想养鸡了小阳走了去哪 不知道诗人哭了他早就该去剃光头而不是在明白这个之后明白什么一切妥协都是得不偿失的!
2 ) 有一个诗人不再写诗,他去养鸡了
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了话剧《恋爱的犀牛》演了2500场的一个视频,导演孟京辉和编剧廖一梅分别上台讲话。
这两个人合作的戏剧数不胜数,但这一次,孟京辉将目光转向了电影,两人合并,完成了孟京辉的电影处女作《像鸡毛一样飞》。
在电影的海报上有这么一个问题:你确信自己幸福吗?
是,不必来看这部电影否,一定来看这部电影由此可见,这依旧是一部关心人类的电影。
在话剧中孟京辉是当之无愧的先锋,但在电影里,他是个绝对的新手。
他在导演自述中说到:“我不太懂镜头运用,不懂用光,不懂胶片,也不懂具体操作,甚至对未来的票房什么的一切都不懂。
”因此《像鸡毛一样飞》更像是一部不停转场的话剧。
孟京辉用新颖的形势讨论了一个并不崭新的话题:理想与现实。
“让那些在欢乐中发霉的人们迅速死亡而让应该成长的孩子们能够成长这一天将会到来他们将用我的诗作为孩子的名字。
”陈建斌的独白配上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照片,让电影的开篇就是充满诗意的。
它讲述了一个落魄诗人来到了一个首都机场附近的小镇,在这里,他的昔日好友,一个曾经的诗人已经成为了一个黑鸡养殖场主。
在这个神秘又怪诞的小镇上,他遇到了一个患有色盲症的小镇姑娘。
欧阳云飞是个创作力萎顿,在生活处处碰壁的倒霉诗人。
在电影的开头,他就丢失了自己的行李还被当成小偷,被问及职业时,他只敢小声说自己写诗。
已经很久没有写出一个字的他已经不敢面对自己“诗人”这个身份。
他握着自己的理想,有迷茫,也有动摇,跌跌宕宕,像一片飘在时代中的鸡毛。
“没有人会等我,没有人会对我抱有希望”,这时他选择放弃,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同学,和他一起养黑鸡,想要彻底融入世俗的世界。
当他遇到了欣赏自己的方芳,他也只能说出“有一个女孩相信我的笔能给她的世界带来色彩,我就只好装模做样得举着那只用完了没墨水的笔,像一个士兵举着没有子弹的枪给自己壮胆。
”这样的话,在面临自己将尽的才华时,他是软弱的。
他害怕被遗忘,害怕不被抱有希望,害怕失败,他在为自己温饱担忧的同时又不愿放弃自己的理想,想要堕落却又心有不甘。
诗人是天生的敏感的理想主义者,更容易受到现实的冲击,但整个片子真的只是讲述一个诗人的纠结抉择吗?
不,是观看这部电影的我们,是众生的最初的理想。
另外两个人物,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两条路。
“在喜欢诗人的姑娘变少以后,陈小阳也从诗人的队伍里消失了。
”陈小阳是个很看的开的人,也很聪明,他顺应着时代的潮流,做了很不同的工作,他的理想也在不停的改变,当欧阳云飞找到他时,他正在养黑鸡,目标是占领北京市场。
“一个人出门不带内裤不带剃须刀,带了一枕头一本诗集。
这就是当诗人的下场。
”他是清醒的,也是物质欲望的代表,不只是他,整个小镇的居民都代表了世俗生活,因为这的确也是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相比陈小阳,方芳的经历更加曲折。
她想成为一名空中小姐,却因为色弱被屡次刷下,整个小镇在她的眼里只有黑白二色。
方芳是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她喜欢番茄,每次都是削去头后插入一根吸管吮吸果实里的汁液,她不愿意品尝番茄本身的味道,就像拒绝接受世俗生活的真相。
她喜欢欧阳云飞,她炽热的心让欧阳云飞再次对生活充满欲望,但她的爱情拯救不了他,她的力量太小了。
电影的结尾没有给我们任何答案。
陈小阳和方芳都离开了,他们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轨迹,陈小阳追寻自己的新事业,方芳寻找自己的颜色。
尽管欧阳云飞最后剃了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光头目光坚定地走在路上,但也只是“坚定”而已,前方究竟存在些什么,理想的生活会有如何着落,一切都是未知,还是那根孤零零飘在空中的鸡毛。
本文由微信公众号上游影视(shangyouyingshi)原创首发,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3 ) 选择或是承受
其实我们不只一次讨论过这类似的问题。
我们常常会想将来怎么办,将来会遇到如何如何多的阻碍,昨天阿pia还跟我说一定让自己想清楚再去做,别浪费自己时间也别让自己后悔。
我说我想好了的。
这样的问题有人需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想,有人只需要几分钟。
这就像欧阳云飞和陈晓阳一样,一个一辈子的理想就是当一个作家,而另一个的理想天天换,所以至今他也达成了好几个愿望。
我需要几个理想?
或者是我能否有那个勇气?
就像欧阳云飞在三十岁的时候学着马雅科夫斯基一样剃了个光头走在灰白色的大街上,他说他至少该有那种坚持的勇气。
虽然我们都知道,不一定真的能做到选择并坚持……回到电影。
最直观而整体的印象就是灰白色,全体涂成白色的房子、深色的衣服、暗绿色的干草地等等等等……拼贴出这个理想匮乏的小镇。
人们都古里古怪,他们比起自己的生意似乎更加关心那个剃头的家伙是不是故意给别人剃到了眉毛,或是用自己的生意来赌气。
看起来就是那么可笑。
欧阳云飞总是抱怨:“你瞅瞅你住的是什么地方!
这镇上都什么人!
都什么旅馆!
什么店什么服务员!
”以及“跑的什么步!
这什么路!
什么桥!
什么空气……什么日子!
什么生活!
”他喊够了,发泄完了,还是要面对。
要面对写不出诗的痛苦、面对生活的压力、甚至要面对马晓阳的逃跑。
这就是生活,就是活生生的现实,压得人皱着眉头喘不过气。
很多人是有理想的。
比如方芳,她不想总是个服务员,她想当空姐,她知道每一班航线,知道上海的天气如何,可她色弱。
“分不清蓝色和绿色对谁会造成妨碍呢?
”“可总有什么地方会出问题的,对不对?
”她自己也知道,有些理想真的是遥不可及,她有的只是坚持的勇气。
而那个结婚的男人(原谅我忘了他的名字)。
他苦苦哀求欧阳云飞给他写一首诗,最后他如获至宝的把裴多菲的诗在婚宴上大声朗读。
为了读出这首诗,他喝了很多杯酒来壮胆。
而到了最后,又以一句毫不相干的话结尾:“最后!
所有的保险丝都换新的了!
”众人鼓掌喝彩……看来,这个时代很多人真的不需要诗……这并不能说明很多人没有理想,只能说这些人的“不需要”为想成为一个著名诗人的欧阳云飞造成了阻碍。
而他自己也越来越匮乏,利用盗版光盘里的作诗软件一举成名然后享受这种成为名人的喜悦,坐在演播室里胡诌一通,参加文人墨客的聚会。
可他是心虚的,成名之前的心虚是因为自己不出名,当他在警察面前说自己是诗人是明显的表现出底气不足,因为没人知道他,也没有人需要他。
成名之后他的心虚是因为那些为他换来荣誉的诗歌并非出自他笔下。
最后那个盗版软件到期再也不能用时也意味着他的理想又如泡影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说起来很可笑,他未成名时表现出的底气不足我也常常有,所以这种心态于我而言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不过往往也容易让我觉得无地自容……欧阳云飞也常想放弃成为一个诗人的理想,当方芳对他说你不应该和别人一样,你就是个诗人!
可欧阳云飞用孩子般倔强的语气回答:“我愿意跟别人一样!
就一样!
”因为他不被别人需要,不会被人记得也不曾被谁提起,这种被忽略的感受比幽闭恐惧症更加恐怖。
他说他其实不是害怕黑暗狭小的空间,而是害怕不被人需要。
正如电影开头那样,欧阳云飞和马雅科夫斯基的画像面对面坐着,一个目光犀利审视着画外的世界,而另一个犹豫不安,缺乏自信。
最后一个西红柿扔到欧阳云飞的脸上,也是扔到画像上,似乎惊醒了这个迷茫在梦中的人,提醒他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而在片子快结束时,这个镜头又重复出现,这时的欧阳云飞再次惊醒,他也许做出一个这样的选择:不管走怎样的路,至少怀揣勇气走下去。
4 ) 出来飞,迟早要落的
让那些在欢乐中发霉的孩子迅速死亡好让应该成长的孩子们能够成长这一天将会到来他们将用我的诗作为孩子的名字-马雅可夫斯基整部影片里出现了四次马雅可夫斯基的照片,而每一次都会在他头上用西红柿印下鲜红的汁液.顺着他的光头缓缓流下,像从眼睛里喷薄而出的怒火燃烧而成的红色泪滴.影片里也多次出现他的诗被反复诵读的画面,那些略带神经质的诗句裹挟着无以穷尽的悲悯狠狠袭来.这算是孟大对马雅可夫斯基的一次致敬.欧阳云飞落拓地来到这个荒谬地让人难以自抑的小镇,里面有漫天横飞的黑鸡和黑鸡蛋,有古怪的小零售商贩,有在路边总是一模一样动作的孪生人,有旅店里怪异的服务员--方芳.他的幽闭恐惧症,他的脆弱敏感,他的神神叨叨,他的不名一文,都让这个诗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就如那个镜头,在游泳池的底部,一双鞋被扔近来,不断下沉,云飞光着脚在里面潜水,找不到出口,光线处理的不明就里,完全没有逃遁的嫌隙,只有在这样的阴暗里永生.这算是孟大对先锋与荒诞的一次致敬.陈小阳开着自己的奔驰,载着黑鸡蛋,拿着大捆钞票,承着无数奖励,但他却突然的失踪,这是一个没有理想却那在路上的生活状态当做一种理想的人.他不偏执,但他也最偏执.他可以毫不顾及地扔掉拥有的一切,然后去一个天外的世界寻找自己追求的东西--新鲜.只有这样生命有了永恒的可能,甚至只是让自己感觉更人类的生存.这就是全部,这无关他是否是个诗人,也无关他是否是个商人,他只是个普通的但稀少的能把理想当做生活状态延续的人,在这一点上,云飞的诗人头衔其实只是一种讽刺,他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懦弱的一分子,诗人是个屁.这算是孟大对理想和偏执的一次致敬.方芳,一个把诗人无限美好化,当然这其实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她从未见过诗人,整个小镇都没有先哲.所以她把这个貌似诗人的落魄汉子当作了自己的太阳.并毫无理由的将此寄予爱情的接楼用做蒙蔽自己时而清醒的神经.她说,你就是我的颜色.她不是色盲,实际上在她清晰明了地审视自己的眼睛之后,毅然离开,她或许坐着最喜爱的飞机离开,或许她就在飞机上当着空乘,再或者她会在不远的另一个小镇继续自己的服务员生涯.当然,这里爱情死亡的姿势无比难看和丑陋,这是一贯以来对这种所谓虚幻美好化作泡影后的矫枉过正.这算是孟大对狗娘养的爱情的一次致敬.云飞早就不是个诗人,他没有这样的天赋,即使他有幽闭恐惧症这样很诗意的精神科疾病.而事实上,这样的疾病更像是他为彰显自己是个诗人而做的一点哗众取宠的伎俩.拿到了能为自己做诗的碟子,在盗版光碟商贩的笑声还没有完全消退的时候便拉上窗帘,把自己关在小屋里(他他妈的这个时候怎么不幽闭一把?),"黑白橘子""后现代诗歌""哲理诗歌"就这样简单的选择就把他变成了新时期的先锋诗人,并且他还得意洋洋地在四处做广告上电视,他不觉得恶心?不,他快活的无与伦比,尽管他自言自语地说周围的每一个人,但,他自己早就和他们一样成了商贩手中碟片的努力。
而这,在他推开厕所门口,一目了然.这算是孟大对当今文艺界的丑恶做的一次讽刺,同时致敬.小镇的电工要作诗,他鼓足勇气,念下酣畅淋漓的诗篇,但人们漠然的心寒,背景灯光变地昏暗低沉,突然他说,小镇所有的保险丝都换新的了.全场欢呼,天空转阴为晴.走出长廊的云飞,回身观望,日光灯诡异地闪烁,一片妖冶的表象.很多......看完这部电影始终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云飞会只买那一种烟,但却总是没有,而他又每次都会选择换一种品牌.为什么飞机的阴影会数词出现在草地上的云飞头上.为什么会把西红柿砸在脑袋上,迸发出血红的汁液.为什么会在最后云飞已然不可能成诗人却还要学着马雅可夫斯基剔成光头.我有很多自己的解释,却没有一个满意.就像方芳的问话,总有一个地方会出错,对不对?答案云飞知道,但他没有说.他只是暴怒,你为什么叫我诗人,我不是诗人,因为我知道要想被称作诗人要过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诗人早就死在另一个世界,而我们苟且在现实的泥淖.生活没有诗意,残缺苦楚只是一个冰封结界里唯一供于品尝的玩物.马雅可夫斯基说过,人应该选择一条自己的道路,并勇敢地坚持下去
5 ) 再回新光
上次去时,新光还没改造,只觉得破破烂烂,《菊豆》那场,人不多,但电影,我很喜欢。
二去新光,还是因为“过电瘾”,改造过之后,感觉比原来“先进”了点。
只是今天银幕用得比例有些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看到《黑咖啡》的单页,心动啊,可惜没搭子。
新光,我肯定要去那看场话剧,一定!
片子怎么说呢,实验风格,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厕所摔了一跤的关系,感觉自己有点坐不住。
关于诗人的爱情故事,很多桥段,分明是在演话剧嘛。
看到了刘晓晔,原来陈明昊就是“小郭”……突然想到一个故事,女生喜欢上一个男生,就因为对方够颓废够堕落。
但是有一天,男生为了能娶女生,开始穿西装打领带,每天朝九晚五。
女生反而开始不待见他了,觉得他变了,觉得他不好玩了……又好比,她喜欢你,只因为你肯花时间陪着她哄着她。
但是为了你们的未来,你开始把一部分时间放在了工作上,她只会觉得你没有原来那么爱她了。
真是矛盾呢,你打动她的地方,也许正是你的天真无知跟青涩,但人不可能一辈子这样,你总要长大的呀……等变优秀了,却发现她还爱着原来的你。
10.03.15凌写于外公家
6 ) 我不是一个诗人
今天看了<像鸡毛一样飞>.脑子里一直回旋着的,是<黑眼睛的姑娘>,<太阳照常升起>结尾那支忧伤的民歌,忧伤得像在路的尽头再没了希望,又像失去了路的尽头看不到希望.云飞在废弃的鸡场诉说出来的那首诗(因为朗读背诵朗诵都不合适,就用了诉说这个蹩脚的词),我一句句听写了出来,原来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一首丰盛而又贫瘠的诗.那是在别人眼里的丰盛,而作者自己诉说出来的贫瘠.这就是诗人,"你自己没有希望,但是可以让别人燃起对你的希望".就像云飞之于方芳.过于纯粹的精神让诗人在生活中找不到出路找不到救赎,却让世人知道精神还能有所仰望.他们像观光客一样在精神的世界里进进出出,觊觎一番,各取所需,只有诗人坚持并怀疑着他们的梦想.其实,我没有看到云飞的才情.话剧般的电影,用话剧般的台词只着重刻画了他的怯懦与彷徨.当他在机场,拿错了包,丢失了证件,没有工作单位,没有人愿意为他证明的时候,一句"我是诗人"在警察前是如此的可笑与狼狈.卖烟的也听不到他说话;一首诗不如一句"保险丝全换新的了"能博得喝彩;赫拉克利特顾城朱自清高尔基莎士比亚全拿去推销黑鸡蛋..........这个有幽闭恐惧症的诗人,在幽暗的房间用盗版光碟炮制诗歌炮制成功,却炮制不掉内心的荒芜.原来在这个现实的任何一处,不论是平庸还是成功,不论是俗人的婚礼还是文人的酒会,都是逼仄得让理想生疼.云飞内心的本质,便是不能靠近,不能相信,不能投入,也活该最后所有的"成功"到头来还是烟消云散.志不同道合的陈小阳突然失踪,寄回来一张明信片证明这部电影还不是魔幻现实主义.方芳离开了.云飞做了一个梦."我再也不想写诗了",云飞,是不是一直怯懦下去,也需要勇气?我不是一个诗人,我只是一个孩子,有着细微和盛大的快乐和悲伤.只是我再没有勇气把它们都表白出来,于是它们都枯萎了.这就是理想主义面对现实主义时的面有惭色又心有不甘.你为什么叫我诗人我不是诗人我不过是个哭泣的孩子你看我只有洒向沉默的眼泪你为什么叫我诗人我的忧愁便是众人不幸的忧愁我曾有过微不足道的欢乐如此微不足道如果我把它们告诉你我会羞愧得脸红今天我想到了死亡我想去死只是因为我疲倦了只是因为大教堂的玻璃窗上天使们的画像让我出于爱和悲而颤抖只是因为而今我温顺得像一面镜子像一面不幸而忧伤的镜子你看我并不是一个诗人我只是一个想去寻死的忧愁的孩子你不要因为我的忧愁而惊奇也不要问我我只会对你说些如此徒劳无益的话如此徒劳无益以至于我真的就像快要死去一样大哭一场我的眼泪就像你祈祷时的念珠一样忧伤可我不是一个诗人我只是一个温顺 沉思默想的孩子我爱每一样东西的 普普通通的生命我看见激情渐渐地消失为了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东西可你只是笑我你不理解我我想我是个病人我确确实实是个病人我每天都会死去一点我可以看到就像那些东西我不是一个诗人我知道要想被人叫作诗人应当过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生活天空 在烟雾中被遗忘的蓝色的天空仿佛衣衫褴褛的逃亡者般的乌云我都把它们拿来渲染这最后的爱情这爱情鲜艳夺目就像痨病患者脸上的红晕
7 ) 《像鸡毛一样飞》台词
像鸡毛一样飞 剧本 独白:让那些在欢乐中发霉的人们迅速死亡,而让应该成长的孩子们能够成长。
这一天将会到来,他们将用我的诗作为孩子的名字。
这是马雅可夫斯基22岁时写下的诗句。
这个仅仅活了37岁的苏联诗人喜欢在人们聚集的地方当众朗诵。
据说他声音洪亮才思敏捷。
那时候的年轻人无论男女都疯了一样的爱他,他们跟着他一起默诵,就像今天的年轻人跟着歌星一起哼唱。
欧阳云飞:这包是我拿的。
我一上飞机我就把我的包放在我头顶的行李箱里,下飞机的时候我就从行李箱里拿了我的包,就是这个包,颜色、拉练跟我那个包一模一样。
我真没偷东西。
警察A:那你的包呢?
欧阳云飞:不知道。
警察B:你能证明这包就是你从行李箱里拿的那个包吗?
欧阳云飞:不记得了,我坐飞机紧张,我真的不记得了。
警察A:那你来北京干什么?
欧阳云飞:看朋友。
警察A:身份证呢?
欧阳云飞:在我自己的包里。
警察A:你是干什么的?
欧阳云飞:没工作。
警察B: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欧阳云飞:写东西。
警察A:写什么东西呀?
欧阳云飞:写诗。
警察A:诗?
你是诗人?
警察B:你叫什么名儿啊?
欧阳云飞:欧阳云飞。
警察A:欧阳……你听说过这人吗?
警察B:没有。
我,听说过高尔基。
警察A:高尔基不是诗人,李白才是诗人。
警察B:李白……那,你都写过什么作品哪?
警察A:对啊,你都写过什么呀?
欧阳云飞:我能打个电话吗?
警察A:多少号?
欧阳云飞:1331010557。
警察A:没在服务区。
欧阳云飞:那我还能再打一个吗?
警察A:说!
欧阳云飞:021,840……02184048381。
小夏,是我云飞。
别挂别挂,求你了。
我现在在北京机场里遇到点麻烦。
我的证件丢了,你跟他们说说,说我是好人不是小偷。
求你了。
警察A:喂,喂你好。
哦,明白了,好,谢谢。
——对方说,从没听说过欧阳云飞这个人。
欧阳云飞:你们这什么机场啊?
机场这什么保安啊?
我丢包了把我当小偷审,有这样的吗?
太不象话了。
陈小阳:不过说实话你挺像小偷的。
欧阳云飞:你才像小偷呢。
陈小阳:哎,你怎么那么弱智呢?
你当场给人写首诗不就证明你是诗人了吗?
欧阳云飞:我当场写首诗?
你以为我跟你似的,写打油诗出身的张嘴就来?
陈小阳:你到这来干吗?
独白:我到这来干什么呢?
从来没听说过欧阳云飞这个人,这说明现在已经没有人需要知道我的消息。
没有人会等我。
没有人愿意对我抱有希望。
只剩下我自己,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找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但是我却不知道,该开始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记者:哎对不起让一让,借过了,好!
电视节目:祖国新貌!
京郊大地春意昂然,科技兴农已经蔚然成风!
一种新型的黑鸡养殖业正在愀然升起。
大学生陈小阳带领农民脱贫致富,使黑鸡养殖在农业产业化的今天有了更大的发展!
黑鸡,不是乌鸡…… 独白:陈小阳还是那个样子,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十年前的青春诗会上。
那时候,他初出茅庐风头正健。
在诗坛也算是小有名气。
在喜欢诗人的姑娘变少以后,陈小阳也从诗人的队伍里消失了。
这些年,他紧跟社会发展潮流,做过所有中国最时髦最有潜力的新兴产业。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他终于找到最理想的事业,养鸡。
电视节目:这种黑鸡蛋的胆固醇含量是一般鸡蛋的百分之十,而维生素E、蛋白质的含量,是一般鸡蛋的五十倍。
相比之下,白皮的鸡蛋完全就是鸡屎。
我要做的,是不让老百姓总吃鸡屎。
我要把白皮的鸡蛋,彻底的赶下老百姓的餐桌!
用健康营养的黑鸡蛋,取而代之。
陈小阳:这只是第一步。
明白吗?
欧阳云飞:哎你这儿有没有荞麦皮枕头?
陈小阳:没有。
怎么了?
(接电话)喂,喂?
哦。
——云飞,行李已经找着了,机场的人送到飞翔饭店去了。
我派人取一趟。
欧阳云飞:不用,我自己去吧。
小国:(被理发的黄毛剃掉眉毛)黄毛!
黄毛:我不是故意的,哎!
我不要你钱不就完了吗?
欧阳云飞:来包好彩。
男小贩:那小子是不是故意的呀?
女小贩:是啊,看把人家眉毛给剃的!
男小贩:啊,啊要什么?
欧阳云飞:我—— 男小贩:小国也真是的!
全镇的人都知道这个王梅她爸要把王梅嫁给这个黄毛,他干吗跑那个店里理发啊?
女小贩:小国就一傻小子,白长那么大个子,哪有人黄毛有钱啊?
欧阳云飞:有好彩吗?
男小贩:要35是吧?
女小贩:万宝路。
男小贩:万宝路?
女小贩:恩!
芳芳(向故障电梯内):哎,有事吗?
芳芳:你没事了吧?
取包做个登记。
姓名?
欧阳云飞:欧阳云飞。
芳芳:年龄?
欧阳云飞:31。
芳芳:性别?
欧阳云飞:……男。
芳芳:工作单位。
欧阳云飞:没有。
芳芳:现住址。
欧阳云飞:鸡场。
芳芳:飞机场?
欧阳云飞:养鸡场。
芳芳:由何处来?
欧阳云飞:外地。
芳芳:哪儿啊?
欧阳云飞:上海。
芳芳:来此目的?
……婚姻状况?
欧阳云飞:未婚。
芳芳:看看行不行,签个字。
欧阳云飞:身份证呢?
芳芳:…… 芳芳:39分。
一次比一次差哦。
小妹妹:噢!
谢谢你。
你怎么不说话?
芳芳:你给的西红柿太小了!
小妹妹:那我下次给你大的。
(抬头)飞上海的。
芳芳:当然不是了。
南方航空767,CZ310,飞香港的。
小妹妹:知道了,谢谢你。
芳芳:一点都不可爱。
小妹妹:好讨厌啊!
……火车开了,带走脸和一张张报纸,带走手、外衣和灵魂,哑孩子在露水里寻找他丢失的声音,就像我在人群中寻找你的踪迹……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听不懂哎!
芳芳:想知道吗?
小妹妹:恩!
陈小阳:云飞,好点了吗?
欧阳云飞:好多了。
陈小阳:药都吃了?
欧阳云飞:吃了。
陈小阳:再喝点水吧。
欧阳云飞:喝过了。
陈小阳:我这儿有鸡汤你喝不喝呀?
慢点,别烫着。
欧阳云飞:你这有没有白鸡汤?
陈小阳:欧阳云飞,我都快烦死了你。
哎,我这就黑鸡,黑鸡蛋,黑鸡汤,你爱喝不喝!
从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照顾你,你都长这么大了还让我照顾。
对,还有小夏。
欧阳云飞:你不要再跟我提小夏,不要提小不要提夏!
不要提!
陈小阳:你跟小夏——分手了?
欧阳云飞:对!
陈小阳:你瞅瞅你混这样!
欧阳云飞:我混怎么了?
你混得好?
你瞅瞅你住的这都什么地方!
今天早上我去取包,镇上都什么人啊?
那都什么旅馆什么电梯什么服务员那都是?
陈小阳:我们这的鸡都是抗干扰型的,你怎么就不如鸡呢?
欧阳云飞:我是人,不是鸡。
陈小阳:说的对,你是人,你还是一诗人呢!
哎那诗人能上床躺会吗?
欧阳云飞:没人铺床我怎么睡?
陈小阳:行,欧阳云飞有你的。
不就是铺床吗?
我给你铺!
我给你铺!
什么呀这都是!
一个枕头!
欧阳云飞:这不是普通的枕头,这是荞麦皮枕头。
陈小阳:一个荞麦皮枕头又怎么啦?
欧阳云飞:能保证我睡个好觉。
陈小阳:能保证你睡个好觉?
还带着呢啊—— 欧阳云飞:你把你的脏手从我的诗集上拿开,快点!
陈小阳:一个人出门不带内裤不带剃须刀,带了一枕头一本诗集。
这就是当诗人的下场。
欧阳云飞:你现在是不是特庆幸自个儿养了鸡啊,啊?
陈小阳:你现在是不是特后悔自个儿当了诗人了,啊?
欧阳云飞:睡觉!
独白:我的孤独,就像失明的人的最后一只眼睛。
年代,星期和日子,我都将忘记。
把自己和一张稿纸关在一起。
田野,树林,小镇,常常有飞机划过的天空,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落脚点。
芳芳:那是辆什么车?
欧阳云飞:桑塔那2000。
芳芳:我说颜色。
欧阳云飞:红的。
芳芳:那辆呢?
欧阳云飞:白的。
芳芳:再后边那辆呢?
欧阳云飞:蓝的。
芳芳:蓝的?
为什么我看是绿的?
欧阳云飞:有可能。
芳芳:我没想成为一个画家,我就想当一名空中小姐。
我把黑色看成了灰色,对谁会有妨碍呢?
我不是色盲,我只是辨色能力弱。
就因为我分不清蓝色和绿色,他们就下了定论,你的人生完了,梦想,也没了。
所有的努力也都白费了。
你还要继续地等在老地方,哪儿都去不了。
我知道所有的航班时间,知道上海的六月爱下雨,巴黎的罗浮宫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是免门票的,我还知道空中小姐的身高,伸手一定要够得到行李架,她们口红的颜色一定要是朱红和玫瑰红。
可这些又能怎么样呢?
一点儿用都没有。
总有一个地方会出问题的,是不是?
总有一个地方会出问题的是不是?
欧阳云飞:生活哪能尽如人意啊?
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比方我吧,我就有幽闭恐惧症。
芳芳:你是个诗人。
我见过你的诗集,和你的枕头放在一起。
欧阳云飞:买种鸡在左手第一个门,买鸡蛋在第二个门。
小国:我找欧阳云飞。
欧阳云飞:你找我什么事?
小国:我……要结婚!
我叫小国,我和,我和王梅要结婚,她是这,这儿的邮递员。
我们都认识很长时间了。
虽然她的父母不太,不太满意,但是我们挺合适的。
欧阳云飞:你有什么事?
小国:这儿的黑鸡真黑啊!
呵,我是小国啊,咱们这儿的那个那个,供电局的,电工,我和王梅我们俩结婚,我们…… 欧阳云飞:你到底,找我什么事。
小国:嘿,嘿,你是诗人,你帮我写首诗吧!
欧阳云飞:这恐怕帮不了你。
小国:那,那,为什么呀?
为什么—— 欧阳云飞:因为我已经不写诗了。
小国:哦!
那,那就算了吧。
欧阳云飞:哎打火机。
医生:怎么样?
你都背出来了?
芳芳:他们换了册子,还说,叫我以后不要再报名了。
医生:芳芳,你年纪也不小了,找个男朋友结婚吧。
芳芳:反正我早晚都会离开这儿的。
医生:是啊是啊,你不当空中小姐,也一样可以离开的嘛。
芳芳:那我不能离开了,到外边还继续当服务员吧。
再说了,我有男朋友。
您见过诗人吗?
医生:诗人?
什么诗人?
芳芳:咱们这儿没出过诗人,连见过诗人的人都没有。
医生,您知道幽闭恐惧症吗?
医生:幽闭恐惧症?
欧阳云飞:来包好彩。
女小贩:没有!
欧阳云飞:那就,来盒中南海吧。
女小贩:没有!
欧阳云飞:这不是中南海吗?
女小贩:假的!
欧阳云飞:那,哪个是真的?
女小贩:万宝路!
欧阳云飞:多少钱啊?
女小贩:20!
欧阳云飞:20块钱一盒万宝路?
芳芳:多少钱?
女小贩:10块!
芳芳:为什么不给小国写诗?
欧阳云飞:你让那小子找我去的?
芳芳:对啊,小国是我小学同学,他下个星期六就跟王梅结婚了,可是王梅她们家非让她嫁给黄毛,小国就想让她高兴一下,能为她们的婚礼感到骄傲一点。
欧阳云飞:你就出主意让他在婚礼上念诗?
芳芳:是啊,怎么了?
欧阳云飞:这主意挺好。
芳芳:就是啊!
欧阳云飞:但我写不了诗。
芳芳:为什么你写不了诗?
欧阳云飞:我现在改行养鸡了。
芳芳: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诗人可以改行养鸡的。
欧阳云飞:现在你听说了。
你以后,再别跟别人说我是诗人了,好吗?
芳芳:为什么呀?
欧阳云飞:因为现在,大家需要鸡蛋不需要诗。
芳芳:需要!
小国就是需要诗!
他就想送王梅一首诗。
欧阳云飞:那他可以给她送两箱鸡蛋嘛!
芳芳:可以!
你可以送给她两箱黑鸡蛋。
欧阳云飞:我可以送给她两箱鸡蛋,没问题啊!
芳芳:你不能送他们黑鸡蛋,你应该送的是诗!
(对女小贩)明天进两包好彩。
欧阳云飞:人不可能两次吃到同一颗黑鸡蛋。
陈小阳:太深奥。
欧阳云飞:无知的黑鸡蛋,无畏。
陈小阳:太调侃。
欧阳云飞: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黑鸡蛋。
陈小阳:太朦胧。
欧阳云飞:你养鸡来我收蛋,双方得利有钱赚。
陈小阳:山药蛋派的,太土!
欧阳云飞:在曲曲折折的荷塘上,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黑鸡蛋。
陈小阳:太没力气。
欧阳云飞:在苍茫的大海上—— 陈小阳:让黑鸡蛋来得更猛烈些吧!
欧阳云飞:黑鸡蛋,还是白鸡蛋—— 陈小阳: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欧阳云飞:是默然忍受白鸡蛋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而出反抗并结束这—— 陈小阳:我要做一颗响当当硬邦邦砸不扁踩不烂蒸不透的—— 合:黑鸡蛋!
欧阳云飞:好!
这个好!
就这个!
陈小阳:好什么呀!
一句广告词你都想不出来。
你这诗人怎么混的。
欧阳云飞:你混得好!
瞅瞅你住的什么地方!
镇子上都什么人,什么旅馆,电梯,电梯里的什么服务员,打算让我写诗!
哼。
陈小阳:云飞,我就是混得再差,也有你一口饭吃。
小国:我要念首诗。
宾客:哈哈哈哈哈哈!
小国:我要念一首诗。
宾客: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 小国:我想念一首诗!!
宾客:…… 小国:送给我的,新娘。
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
我愿意是花,如……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
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
我的爱人!
如果你是天空,我愿意变成天上的星星。
我的爱人,如果你是邮递员,我愿意是你背包中的信,跟着你的自行车,到处漫游,永远不被投递,如果你是新娘,我愿意付出我所有的努力,成为你身边的新郎!
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所有的保险丝,都换新的啦!
宾客:喔!
好!
…… 陈小阳:那边还有事。
乐队:黑芝麻哇白芝麻哇哇白芝麻白芝麻黑芝麻哇…… 陈小阳:来来来,你就缺这个,这个,壮阳的!
喝!
乐队:今儿我把它喝了,啊,你就得给我们赞助点。
陈小阳:这句话我听一晚上了。
我就实话实说啊,我就是郊区一个养鸡的农民。
乐队:你以前也是一诗人,哎,哥儿几个都读过您的诗,特崇拜您。
我们现在,就缺这两万块钱的赞助费。
陈小阳:呵!
两万?
咱们先算一个帐啊,一只黑鸡蛋的基本批发价是两毛三。
乐队:两毛三。
陈小阳:防疫、养殖、饲料、包装运输是两毛,加在一块,我要挣一万块钱,得卖出多少黑鸡蛋?
乐队:两块五两块一…… 陈小阳:这么说吧,你们打算,从我这搬走多少黑鸡蛋。
乐队:嗨!
乐队:干吗呢这是?
欧阳云飞:没事没事没事。
乐队:嘿?
啊,他也是拉赞助的?
欧阳云飞:我们小时候都写过一篇作文叫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是当一个文学家像鲁迅那样。
而陈小阳的理想每年都变。
所以他的理想已经实现了很多次,而我的理想,还依然是个理想。
芳芳:苏联诗人…… 欧阳云飞:现在没人读他的诗了。
芳芳:他是白天写作还是晚上写作?
欧阳云飞:什么意思?
芳芳:每个诗人都有他自己的写作习惯。
托尔斯泰是晚上写作,杰克伦敦是早上写作,你呢?
欧阳云飞:我是翻着跟头写作。
嘿嘿,年轻的时候人人都容易产生梦想,年轻的时候人人都是诗人。
但诗人没什么用。
芳芳:有用。
欧阳云飞:那你说我有什么用呢?
芳芳:颜色。
你是我的颜色。
独白:有一个女孩相信,我的笔能给她的世界带来色彩。
我就只好装模做样地举着那支用完了墨水的笔,像一个士兵举着枪,给自己壮胆。
盗版人:站住。
别动。
看看有没有警察。
对,前后左右仔细看看。
哦往上看,往上,往上。
呵,哥们,要盗版光碟吗?
欧阳云飞:不要。
盗版人:哎哎等会等会等会…… 欧阳云飞:哎,哎!
盗版人:来两张吧真的你绝对需要。
听我说!
欧阳云飞:我不要!
盗版人:你人生各个阶段都需要的,尤其是你尤其是你。
你绝对需要,我什么都有啊!
欧阳云飞:那有教人写诗的吗?
盗版人:嘿嘿,你是个诗人。
欧阳云飞:你怎么知道?
盗版人:10年前,你得到它,你需要付出你的灵魂。
可现在,你得到它,只需要付出10块钱。
欧阳云飞:好吧,我要我要。
欧阳云飞:没什么。
这是书架。
书架上都是书。
没什么,真没什么。
芳芳:喂,你去哪儿了?
我等了你很长时间了。
欧阳云飞陈小阳:欧阳云飞,陈小阳,上台鞠躬!
勾肩搭背,你鬼鬼祟祟,半夜三更,你为啥还不睡。
捡块破木板,拼呀拼张床,床上的虱子排呀排成行。
有人在洗澡,被我看见了!
恩哪哪—— 陈小阳:我回来啦!
欧阳云飞:我们回来了!
陈小阳:三天,黑鸡蛋销售一空!
欧阳云飞:全卖光了!
陈小阳:都是老太太买的。
欧阳云飞:还有老头儿!
陈小阳:为什么卖得这么好呢?
欧阳云飞:为什么呢?
陈小阳:为什么呢?
欧阳云飞:因为广告词写得好。
陈小阳:说的对广告词写得好。
是谁写的呢?
欧阳云飞:我当然是我。
陈小阳:肯定是我写的。
我给大家唱首歌,肯定是我写的。
欧阳云飞:我给大家作揖了,肯定是我写的。
陈小阳:我给大家鞠个躬,肯定是我写的。
欧阳云飞:我给大家跪下了,肯定是我写的。
陈小阳:谁呀!
欧阳云飞:怎么了芳芳?
陈小阳:怎么了?
芳芳:我们家云飞不跟你干这些事。
陈小阳:这,这不能跟我干这些事。
欧阳云飞:哎小阳!
小阳!
陈小阳:没事,我没事我没事,没事,你忙。
欧阳云飞: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小阳?
芳芳:你看看他都带你干了些什么?
洗澡,桑拿,唱歌,跳舞,陪吃陪喝,这些是你该干的事吗?
他会把你变得和其他人一样的,你知道吗?
欧阳云飞:我愿意跟别人一样。
芳芳:你不能变得和其他人一样。
欧阳云飞:就一样。
芳芳:你不能!
你是个诗人!
欧阳云飞:什么诗人,实话告诉你吧,婚礼上那首诗就根本不是我写的,那是裴多菲的诗,三年了我一个字都没写过。
芳芳:你就是个天才的诗人!
哑孩子在露水里寻找他失去的声音,就像我在人群中寻找丢失的你一样。
能写这样诗句的人就是天才!
欧阳云飞:我神经衰弱没有我的枕头我就睡不着觉,我还有幽闭恐惧症。
我怎么可能是诗人我?
干什么你?
开门!
开门!
开门!
芳芳:我知道幽闭恐惧症,就是不能忍受狭小的空间,不能长时间地呆在黑暗封闭的屋子里。
你不能坐电梯,不能坐飞机,在不适应的环境里面,你会心慌,会吼叫,甚至会盗汗有的还会昏厥。
可是这些都是会治好的,你怕什么呢?
你看你现在。
独白:狭小的空间,封闭的飞机,晃动的船体,我从来就不害怕。
我害怕的是另外的东西。
不被重视,被人群抛弃,没有才能,成为一个失败者。
谁不害怕呢?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嘉宾:诗人,欧阳云飞。
男小贩:嗨,这不是跟芳芳好的那个男的吗?
欧阳云飞:——诗歌的一种胜利—— 旁人:嗨,他也能出名?
主持人:作为一个诗人您怎么看今天的这个时代?
服务员:上次被关到电梯里了。
陈小阳:你能会儿啊。
欧阳云飞:诗歌需要永恒的革命,每个诗人,每一个诗人总是在不断地使自己眼前的这个世界变得陌生化,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颠覆—— 陈小阳:欧阳云飞你真行,你就胡说八道吧。
欧阳云飞:我现在想谈的是一种大诗歌的概念。
广告:像白的一样白,像新的一样白,像刚搬进来的时候一样白。
爱家涂料。
欧阳云飞:我不行了,我撑不住了,跟你在一块儿我觉得难受。
我不是说你不好,你很好。
但我不是你想要的那种人你明白吗?
我以为我自个儿是个成功的诗人,我太想成功了,我太想让你为我感到骄傲了。
因为是你让我对生活又产生了欲望。
可是我越这样想,就越没有戏。
算了吧。
咱们算了吧。
芳芳:你是我的红色,就是太阳落山时候的颜色。
你是我的蓝色,他们形容的,大海的颜色。
你是我的粉色,就是桃子成熟时候的颜色,你是我的蓝色,他们形容的天空的颜色。
你是我的颜色。
你是我的白色,这个我知道,是雪花的颜色。
黄色,我也能够分辨,是我们皮肤的颜色。
你是我的颜色,所说的红黄蓝白都是你。
你是我的颜色,所说的红黄蓝白都是你。
还有黑色,这些羽毛的颜色。
欧阳云飞:防疫站的人来了?
工人:来了。
欧阳云飞:那小阳,在哪呢?
工人:不知道我跟他联系不上,没联系上,他手机关了。
欧阳云飞:他没跟你在一块?
工人:没有。
欧阳云飞:他没跟你说什么?
工人:什么也没说。
欧阳云飞:这病鸡有多少只啊?
工人:三四十只。
都已经隔离了,不过很快就会蔓延。
欧阳云飞:我我,我给他打个电话。
……没信号。
工人:哎你赶快去跟隔离,隔离病鸡,你们赶快把所有的病鸡都分离出来,不能让它们再…… 独白:陈小阳失踪了。
谁也找不着他。
他想走就走了,所以寻找是没有用的。
他能抛下一切这样离开,说明我一直看低了他。
我们常常会这样,就算对最好的朋友,也会如此。
欧阳云飞:你为什么叫我诗人?
我不是诗人。
我只不过是个哭泣的孩子,只有洒下沉默的眼泪。
你为什么叫我诗人?
我的忧愁,便是众人不幸的忧愁。
我曾有过微不足道的欢乐,如此微不足道,如果我把它们告诉你,我会羞愧的脸红。
今天我想到了死亡。
我想去死,只是因为我疲倦了,只是因为大教堂的玻璃窗上天使们的画像让我出于爱和悲而颤抖。
只是因为,而今我温顺得像一面镜子,像一面不幸,而忧伤的镜子。
你看,我并不是一个诗人。
我只是一个想去寻死的忧愁的孩子。
你不要因为我的忧愁而惊奇,也不要问我,我只会对你说些,如此徒劳无益的话。
如此徒劳无益,以至于,我真的,就像快要死去一样大哭一场。
我的眼泪,就像你祈祷时的念珠一样忧伤。
可我不是一个诗人。
我只是一个,温顺,沉思默想的孩子。
我爱每一样东西的,普普通通的生命。
我看见激情渐渐的消失,为了那些离我而去的东西。
可你只是笑我,你不理解我!
我想,我是个病人,我确确实实是个病人,我每天都会死去一点。
我可以看到,就像那些东西,我不是一个诗人。
我知道,要想被人叫做诗人,应当过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天空,在烟雾中被遗忘的,蓝色的天空,仿佛衣衫褴褛的逃亡者般的乌云,我都把它们拿来,渲染这最后的爱情。
这爱情鲜艳夺目,就像痨病患者脸上的红晕。
欧阳云飞:她肯定是去海南,晒太阳吃螃蟹了。
小妹妹:芳芳姐姐说,她再也不回来了。
独白:芳芳真的没有回来。
她辞掉了饭店的工作坐上她喜欢的飞机,走了。
最近飞机调整了航线离小镇越来越远了。
飞机飞过的时候,我会想起她。
也许她正在飞机上往下看呢。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院子里长出一棵树,树上长满了一首一首的诗,都是真正的诗。
一张张写在白色的稿纸上,在风中哗哗作响。
我和芳芳,就提着篮子在树下摘诗,好大的诗啊!
陈小阳寄来一张明信片,只是道一声平安,他没有说他在哪儿,反正,你不必为他担心,他总是有新主意。
欧阳云飞:来了。
小国:芳芳有消息吗?
欧阳云飞:没有。
小国:你是不是要走啊?
小国:王梅怀孕了。
欧阳云飞:恭喜你。
小国:还得请你帮一个忙。
欧阳云飞:你说。
小国: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吧。
欧阳云飞:好。
小国你是姓?
小国:马。
欧阳云飞:马…… 欧阳云飞:我再也不想写诗了。
陈小阳:我再也不想养鸡了。
独白:我31岁的时候,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剃成了光头。
我知道我可能永远都不了他那样的诗人。
但我像他一样,剃成了光头。
他曾经说过,人,必须选择一种生活并且有勇气坚持下去。
我希望,至少能有他那样的勇气。
8 ) 我只是一个温顺 沉思默想的孩子/我爱每一样东西普普通通的生命
终于想到把这首诗一字一句截下来。
电影,反复的看,反复地听。
想要抓住什么?
或者只是回顾or沉默。
第一次注意到电影的英文名字:《Chicken Poet》——你为什么叫我诗人?
我不是诗人我不过是一个哭泣的孩子 你看我只有撒向沉默的眼泪你为什么叫我诗人?
我的忧愁 便是众人不幸的忧愁我曾有过微不足道的快乐如此微不足道 如果把它们告诉你 我会羞愧得脸红 今天我想到了死亡我想去死 只是因为我疲倦了只是因为大教堂的玻璃窗上天使们的画像让我出于爱和悲而颤抖只是因为 而今我温顺得像一面镜子像一面不幸而忧伤的镜子你看 我并不是一个诗人我只是一个想去寻死的忧愁的孩子你不要因为我的忧愁而惊奇你也不要问我 我只会对你说一些如此徒劳无益的话如此徒劳无益 以至于我真的就像快要死去一样大哭一场我的眼泪 就像你祈祷时的念珠一样忧伤可我不是一个诗人我只是一个温顺 沉思默想的孩子我爱每一样东西普普通通的生命我看见激情渐渐地消逝为了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东西可你耻笑我 你不理解我我想 我是个病人我确确实实是一个病人我每天都会死去一点 我可以看到就像那些东西 我不是一个诗人我知道 要想被人叫做诗人 应当过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生活天空 在烟雾中 被遗忘的蓝色的天空仿佛衣衫褴褛的逃亡者般的乌云我都把它们拿来渲染这最后的爱情这爱情鲜艳夺目 就像痨病患者脸上的红晕……
9 )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来寻找黑鸡蛋
“我们小时候都写过一篇文章 叫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文学家 像鲁迅那样而陈小洋的理想每年都变 所以他的理想实现了很多次而我的理想还依然是个理想”当 诗歌不再是信仰与热爱而成为生活的一种装饰 是获取名利的手段之一那是真的大量世俗生活的场景 不协调的搭配 摇晃的电梯 废弃的厂房 暧昧的酒吧 人们天真的理想在 世俗生活的淹没下摇摇欲坠“你是我的颜色” 我喜欢这句话
10 ) 幻光
顾城:我的幻想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
1969年(北京)
臧克家说: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
明石海人说:像生于深海中的鱼族,若不自燃,便只有漆黑一片。
以上。
P.S.片尾独白:我31岁的时候,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剃成了光头。
我知道我可能永远都成不了他那样的诗人。
但我像他一样,剃成了光头。
他曾经说过,人,必须选择一种生活并且有勇气坚持下去。
我希望,至少能有他那样的勇气。
31岁那年,为了曾经惦记过的这段台词,我再度剃了个光头。
2019.5.27 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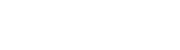





















2008.4.11.23:09...这个&#34;还行&#34;是感情分...孟京辉+廖一梅.陈建斌+秦海璐.唯美的意识流.但总也不及马雅可夫斯基...
虽然很喜欢孟京辉的话剧,但还是感觉这种表现形式不适合电影,太顾顾弄玄虚了,电影是一种叙事性的语言,可以形式可以创新,但不能僭越内容
诗人靠什么收入?
3.6分。秦海璐的表演加分了。
原来片名说的不是影片的内核,而是影片的情节和表现方式。
诗歌已死,你看马雅可夫斯基也流下了蛋黄泪。
孟京辉你真骚
人,必须选择一种生活并且有勇气坚持下去。我希望,至少能有他那样的勇气。
孟京辉廖一梅两口子是文青文艺病的集大成者,矫情作逼,鸡毛当令箭的举轻若重者。演员表演很不错,动画那一段非常好玩。对诗人的理解连门都没入。马雅可夫斯基这种三流诗人,竟然被当成偶像。
难看至极,故事性极差
对我来说此片不是一般的难看。相比之下陈建斌就要聪明很多。
有点像话剧。时间:200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RpF6Hf9D74
我的观后感是,这是一部主题先行的电影,虽然它讨论了理想和生活,但我感受不到生活的烟火气,也没太感受到理想的火花。可它有对于艺术家的几乎所有刻板印象,以及矫情和极端形式主义。一个而立之年的男主,江郎才尽且虚荣,在片中看不到一点才气纵横或有天真深邃思想的影子,时刻在大谈特谈理想。我想说,做不出诗来,会不会是生活的大锤还锤的不够狠?毕竟,文章憎命达嘛。
马雅可夫斯基 黑鸡蛋 D版
2008.6.19 大量镜头缺乏前因后果,剪的乱也应该有内在的联系啊。有些表现手法特别好,有感觉。
呵呵。两星都给多了。
她爱上诗人,是爱的那个人,还是自己心中的浪漫诗意呢?
孟理解的诗人像这部电影一样做作得不知所云而无病呻吟。
很孟京辉的舞台感,诗意渗透在现实的夹缝里,嘀嗒出一种黏糊的败落与固执。写诗,养鸡,一体两面,曾经的文艺气质猛地撞到市场经济的横肉上,进退维谷,赢家唱着跑了调的流行曲式哀乐,败家拧巴在五斗米也换不来的馊味字句里。八十年代风靡的先锋,那种归根结底为不甘却又无力的一时锐意,跨到新时代,成了最末最末的一股跫音。什么都没了,但你看镭射光盘、掌上电脑、澳洲鸵鸟也曾唱过乡镇人间的未来,二十年前的蓬勃乃至疯狂里,我们迎接当下土味的真实,在诗歌成为一种顶无用的假把式,甚至徒留光头模样的空壳后。那时候他们也青春,尽管滑溜的陈建斌演21岁是死活说不过去的,那时候,秦海璐、廖凡的演技亟待雕琢,那时候,大家都还有些想法,不像现在,乃至主创,也空余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