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渊而立》剧情介绍
利雄(古馆宽治 饰)和章江(筒井真理子 饰)结婚多年,共同养育着女儿萤(筱川桃音 饰),虽然生活平静毫无波澜,但夫妻两人之间早已经没有了感情的交流,仅仅维持着婚姻的空壳。利雄的朋友草太郎(浅野忠信 饰)出狱后来到利雄的工作室干活,寄宿在利雄家中。一边是冷淡的丈夫,一边是和善温柔的同居人,内心空虚而又寂寞的章江很快就在草太郎的攻势之下沦陷了。 然而,当章江拒绝了草太郎的求欢后,草太郎便就此失去了踪迹,而萤亦遭遇了意外,余生唯有在轮椅上度过,利雄和章江不知道草太郎到底去了哪里,只知道萤的意外和草太郎有着脱不了的干系。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佐佐木在我脑海中莫斯科陷落恐龙王国修女2首尔怪谈花飞尽、归不归樵夫故事为家而战山无棱天地合爹地机器人8号日常系的异能战斗大梦西游之五行山传颂之物二人的白皇福冈恋爱白书10美女也愁嫁校花的超级保镖之无极诀病毒32秒傲骨贤妻第六季魔法少女奈叶Detonation校花与野出租边境何帅的爱情丹特丽安的书架OAD奥运梦守望的天空入侵之战我的女神永遠的二人OAD01无尽的边界玩伴猫耳娘
《临渊而立》长篇影评
1 ) 算不过来的帐
听上去很无聊的故事,看上去也略无聊的情节却完全不闷呢。
电影给我很强烈的压抑感,那是我每次去欧洲都有的感觉,虽然这不是舒服的感受,但是达内你们赢了。
蓝天白云大太阳,处处光鲜亮丽,但我身处其中,整个人都不舒服,我给自己的解释是身处异乡,出差劳顿,吃得又差,所以每次要去欧洲出差,我都起码提前一个月忧郁症爆发。
看了这部电影,突然我觉得开朗了,我在欧洲(法国/比利时)的压抑情绪不完全是我侨情吧,听到法语那调调我就开始浑身不得劲,去德国,听到德语我可没那么不对劲。
我其实不是很说的清楚这种压抑的来源,经济政治问题和那块地方人们生活态度的矛盾,造就了一个大家都不提,但弥漫着的活到哪是哪的情绪吗,我真的不太懂怎么回事啊。
看看电影里的情况,16个人,每个人1000欧,每个人的年终奖是8000RMB不到就跟这钱要了人命一样。
反过来算,每个人少了1000欧,那女主第二年的工资+福利总共13万RMB不到,她有了这点工资就可以半养活俩孩子加一栋房子了,我真心算不过来帐来了,亲,你要么来上海找工作算了。
马里昂演技精湛,整个电影就她一个人的戏码,赶上去年蓝色茉莉的女王了。
2 ) 色彩真美
说起来,我和达内兄弟的电影还是挺有缘分的。
几年前我在电影学院考试时看过一段影片,那是我当时所看的为数不多的法语片,看完老师让按照自己的感受给电影起名字,当时瞬间浮现在我脑海的名字便是《他人之子》 。
我之前并不知道达内兄弟,更没看过他们的电影,只是那段影片的情节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慢慢对故事的细节也记忆模糊了,但色调和氛围一直停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直到看完《两天一夜》 ,我总是觉得肯定在哪看过同一导演的作品,结果竟然就在达内兄弟的履历表里查到了《Le Fils 》(他人之子) ,2002年的片子,正是我的考试题目,而且还找到了另一部彻底忘记是在哪看过的电影——2005年的《孩子》 。
这种潜意识的联想挺有趣,很多时候看电影也并不是单纯为了知晓情节,一段影像对情绪造成的影响可能才是挥之不去的。
我当然喜欢看情节更富冲击力的东西,但对于此类电影我将它视为拥有一种接近于文学作品的魅力,同样也为导演的个人风格能够对观众产生如此的影响表示敬意。
另一方面,我很感谢我的女神歌迪亚,再次与达内兄弟相遇完全是因为Deux Jours, une nuit的女主角是她,而且由她塑造桑德拉这个人物简直再合适不过了,她的表演与影片是浑然天成的。
我想我应该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对这样一个故事看得目不转睛,所以我试着分析了一下。
《两天一夜》的焦点很明确,清楚简单地交代了女工桑德拉面临下岗困境急需得到同事的投票支持,结局只有两种可能:留下或者走人。
这样的结构非常棒,它使得女主角争取选票的进展过程张力十足,并没有刻意制造戏剧性和悬念,却能令观者感受到自己与片中人物的命运息息相连,发自内心去渴望她获得最终的胜利。
我认为欣赏这类现实主义的作品最大的快感便在于此,即压力不是来自导演,而是来自观者个人的愿望。
虽然我这几年看过的法文电影少得可怜,不过每一部倒都是精品,每一部都独具西欧国家的特色,它们给我留下了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印象。
或许《两天一夜》这种不急不火的姿态在达内兄弟的作品中是一种常态,不过在我看来真是妙不可言,我喜欢它每一个镜头,还有它场景里的每一处细节,总是会惊叹导演捕捉美的功力。
所以这个故事拍出来丝毫没有乏味压抑之感,反而处处充满了清新和生机。
歌迪亚在片中并没有为女工的身份特别改变形象,她质朴憔悴但依旧利落整洁,事实上她蓝牛仔裤和糖果色背心的样子非常动人,却又极具说服力。
我觉得每个看到她的人,就算没接触过她以前主演的各类角色,看到她的桑德拉造型也会很喜欢,贵在贴切真实。
这种效果当然也和电影的整体色调分不开,它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干净,轻松活泼的明亮色块,纯净的空气和透亮的阳光,尽显自然环境之美,也衬托起人物所面临的困境。
电影的结尾某种意义上算是以悲剧收场,不过这种对美的准确捕捉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哀伤的情绪,给观者心灵的慰藉,将故事的温度掌握得恰到好处。
就是这样一个发生在两天一夜封闭空间中的小故事,完成度却是比较高的,除了细腻流畅的画面,还有对不同人物的精准诠释,以及对现实的敏锐感知和理性剖析,一切都做得尽善尽美。
《两天一夜》又一次为我展示了欧洲导演品格高尚的一面,他们真正将电影当成一门艺术,或是一篇社会论文,创作得严肃又用心。
3 ) 人情冷暖
就在过去不久的时间里,我也同样地被别人选择着,但不是选我和钱,而是我和另一个人。
那是开学时候,要评上一年奖学金,按上一年成绩排名我理应拿到,但是却半路杀出个从来没有过的规则,说要综合以往的成绩,综合回来,我正好被砍掉了。
我们班班长知道这不公平,决定以投票进行,评我和另一个男生。
五千块的奖学金说多其实也不多,只是我当晚觉得这规则很不公平,哭了一晚,都后来,我的投票也输掉了。
我没有很在意那五千块,也快要忘记这件事了,只是看到《两天一夜》这样的投票时,我又再一次想起这件事。
尤其是当玛丽昂歌迪亚抽泣着说:“我跟她关系还不错,她连话都不跟我说”的时候,我想起了和我一起被投票的那个男生。
我曾经认为他是我在大学时期最好的异性朋友,没有之一,可就在奖学金评选那段时间,所有人都来跟我说这对我不公平,希望我不要难过的时候,他却一句话也没有跟我说过。
后来我跟学长谈起这件事,学长以过来人的姿态对我说只是因为我付出得太多了,只是我一厢情愿,其实在他的心里我可能还没那五千块重要。
我第一次很切身地体会到人情冷暖。
这样的事情,以后可能还会经历更多,我没办法拒绝,我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
可是我仍觉得很难过,我们才大三就已经这样功利。
我庆幸的是,我跟女主一样坚强,不至于被这样淡薄的人情给粉碎掉。
后来我主动去找那个男生玩,看起来和好如初,但是我知道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了,我的感情不能交给一个认为钱比人重要的人。
在我心里,朋友远比这些身外之物重要,我也很希望我在别人心里能重要得过这些东西,在我觉得疲惫困顿时伴我走过艰难的时光。
4 ) 为了生活赢回尊严
《两天一夜》这是一部描述经济萧条下比利时中产阶级工人生活的影片。
女主角生病后再回工作岗位,被老板和同事歧视,在让她离职和1000欧元的投票中,生活不济的同事们选择了后者。
她为了得到这份能减轻生活负担工作,放下尊严去求老板和同事们再给她一次投票的机会,让她留下来。
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可她的新的生活已经开始。
影后玛丽昂歌迪亚脱去了她明星的光环,完全变身为一位略显病态为了生活奔波的普通妇女,犹豫羞于开口的表情,举手投足甚至痛苦精神崩溃自杀,把这个人物刻画的入木三分,为影片曾分不少。
当然导演的镜头也十分克制,平实尽显真实。
这部电影也让我预见了自己以后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为了生活,尊严、梦想、现实,我会做出什么呢。
5 ) 現實永遠是悲喜交加
两天一夜,对没有强烈风格的片子个人一直不太感兴趣,此片胜在朴素真实。
观片中不自觉把各人物性格特徵记录,里面蕴含了社会中各种基本人格和所处环境压力。
人物出场顺序也顺应一定的规律,永远会是跌宕起伏,没有持续的失败和成功,落魄的后转身总会得到眷顾,欣喜离开时又会出现犹豫的声音。
首先第一个卡戴尔的肯定使之后的路得以延续。
第二个威利 ,典型的忠厚善良配上咄咄逼人的老婆,权利不在其手,配偶为主要压力。
第三个,婚后和男朋友白手兴家需要资金,也不是自私,谁能打扰爱情初生的甜蜜的,这段时间是最坚不可摧。
第四,纳狄娜,很多人在面临问题的第一选择即是逃避,因为尴尬,因为友谊,因为是之前最好的朋友。
以为逃避是暂时的舒缓,殊不知是对自己永久的折磨。
连续的拒绝后女主情绪跌入低谷,此时曙光必然降临,提姆尔。
见面后是惭愧的眼泪,之前的抉择一直让他寝食不安,之前的抉择是对利益的第一反映。
同做一件事,事后的态度便是善恶之分。
第六个希查姆,结合之后让-马克的反应,私认为此人是最恶念的一个,决绝的同时捏造谣言让女主认为事已抉择不可能会有改变。
之后的七八伊冯和吕西安代表善恶中的对立,并把矛盾的勾心斗角中加上了暴力的元素,把矛盾推向顶端。
之后的安妮,便是至善的存在,本来的犹豫不决源于老公的极力反对,之后在女主堕入绝望,服药自杀之际,把女主从悬崖边带了回来。
她决定离婚,帮助了他人更释放了自己。
其实人性真的本都是善只是现实有太多枷锁束缚,放下种种,最后会发现得益最大的可能是自己。
之后第十个人,例牌成功后的的拒绝,直截了当的拒绝。
阿尔封斯文,一个传统的新人,害怕被排挤甚至不敢抉择,心底最为清澈,始终没有考虑过奖金的问题,只求平稳抱住工作,并最终还是投了同意票。
随后一个给了犹豫不决的答案,为结局留悬念。
影片中女主没有过人的意志,很多时候靠著家人朋友鼓励前行,并还有过自杀的举动。
不是寻常的英雄套路,没有主角光环强大到足以抵御一切,接著迈向成功。
她就是我们芸芸众生,随著海浪逐流,心态随人随事改变,而真实的世界里本来就是善恶交替,悲喜交加。
普通的人经历著普通的生活,最后结局是失败,但捍卫了自我的尊严。
就是此片的真实所在。
6 ) 抑郁形象之下
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捷尔吉(Lukács György)针对写实主义作品曾提出“典型性”(typicality)这一说法。
所谓的“典型”,根据Lukacs所说,是指写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既代表着他们独特的虚构性存在,却也是在某一个大社会历史环境下具有某种社会群体性特征和历史辩证进展特性的具体化存在形式。
而毫无疑问,从Lukacs的典型性角度出发来看,电影《两天一夜》的即将下岗的女主角Sandra及她在这两天一夜里所拜访的同事便是这样一种具有写实主义特点的存在。
玛丽昂•歌迪亚扮演的女人Sandra是一个曾患有抑郁症(depression)的,正在恢复中却不得不因为所在公司的不景气即将被迫下岗的人。
她偶尔歇斯底里、精神不稳定、焦躁、疑虑、自我否定、依赖药物,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缺乏足够的理智操控力和过多的精神能力和能量”。
她代表了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的的资本社会中一群注定被边缘、被社会主流群体远离和漠视的精神病患者:他/她们往往因为精神疾病而不被社会所接纳,在工作中很容易被列入首位被排斥者,他们的治疗及康复得不到众人的信任,而这些怀疑和排斥往往又加重他们的病情,如此恶性循环下去。
而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社会贴上一个共同的标签——“抑郁症患者”,在这个标签之下,人们对他们的了解和印象也无法脱离病症症状。
他们被抽象成一种病的具体人物化代表,而个人主体(subjectivity)的身份(identity)不再重要。
而在达内兄弟镜头下的Sandra又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具有社会历史性群体化的代表,她屡次神经质般情绪决堤的另一面,是她面对自己孩子时忍痛的坚强,她整理孩子床铺时的细心周到,她对避她不见的旧好友的理解宽容……无处不表现了她独特的主体性。
除了在她嚎啕大哭及过量吞服抗抑郁药的场景,她去同事家一次次的拜访和说服也逐渐剖丝抽茧地透露出她在与人相处、遇事待人时独特的处理方式与做人原则。
她的形象在达内兄弟一个个巧妙的特写镜头下不再止于一个单调的抑郁症康复女性,而善良、试图坚强起来、愿意帮助他人、宽容……这些带着脉脉温情的人性的一棱一角也逐渐在她身上丰满起来。
《两天一夜》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其故事情节的平淡叙述继续与好莱坞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商业模式相背离。
大量使用的人物特写镜头也是对演员的巨大挑战。
可也正是他们大胆使用的特写镜头和安排巧妙的故事结构,让人物复杂的情绪真实而鲜活地表现出来,每一个镜头彰显了一个个细节,看似平淡,却让人回味无穷。
7 ) 欧洲下岗工人的不屈抗争记!
欧洲穷人偏极端的情况是害怕下岗去领救济金,而我天朝的呢?
1,,不得不说,这的确不是达内兄弟的最高水平,也不是玛玛最高水平的发挥。
但是,又不得不说,即使这样,双方都依旧保持了较高的水准。
2,达内兄弟标志性的手提摄影,短小精悍简洁有力的故事,不算太长的片长。
这些都成了达内的一项利器,从这点来说过,dogema95宣言的宣誓人拉斯早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宣誓,相反达内兄弟在这方面做得还算不错,基本属于巴赞一派的忠实笃行者。
这部片子从剧情上来说,是极其俗套的,冲突单一,却贯穿片子始终。
剧本上,完全谈不上什么新颖和奇幻,但也恰恰四平八稳始终扣着主题。
无怪乎,戛纳观影后众人觉得太平淡,没有达到期望。
其实,达内兄弟的哪部片子不是这样呢?
淡如水,又不止水,恰恰水能止渴,而胜过华丽丽的饮料呢?所以,故事就是在这样围绕一个下岗女工人求生存的再次拉票上展开,支线不能说没有,但主线始终如一的贯穿着。
平淡着,你觉得太平淡时又恰恰不平淡,是那种你看着看着,一路大喊失望时又恰恰总是让你燃起某些希望的片子。
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还是在达内的小径里穿梭吧。
故,我恰恰觉得看完之后,俗套的剧情,俗套的发展,俗套的结果,俗套的结尾下恰恰又有了那么一些惊喜,算得上是一部上乘作品吧。
3,达内兄弟追随着巴赞老师的真实性传统,追随着把握暧昧生活的传统,更希望以不做过多干扰的方式让观众去发现兴趣点。
我看到了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
其一是那个后面为了帮玛玛而跟老公闹到离婚的妇女,按理说,她们应该很熟,一方各诉各的苦水后,她说愿意尝试跟老公沟通一下,于是玛玛开心地走了,她却说我去记下您的电话号码!
这个地方吧,很有趣,你觉得是达内兄弟故意刻意安排的吧,也的确像,但恰恰这个地方又隐去了那种刻意安排的痕迹。
这就是一种生活的常态中,不常态的“爆点”在,达内兄弟总算没有辜负巴赞老师的期望啊。
同理,也可以看到帮助玛玛的丈夫无微不至下,玛玛突然说你在可怜我,然后抛出我们三个月没有做爱了。。。
这跟前面那个点何其相似,突然一下出现了尬尴,出现了所谓的戏剧化时刻。
但达内兄弟并没有就题发挥,至于好莱坞的“大师”们那肯定会对此痛批一番吧。
这种戏剧时刻点到为止,立马进入下面的话题。
这种更追求真实性的做法,事实上并未降低电影的可看性,只是看观影者自身的心态和敏锐度罢了。
毕竟,巴赞先生提出的表达”暧昧生活“时他并未把整个观众群体包括进去,这话一出,事实上对观影群众做了区分。
这点我们又何必纠结于观众的高下呢?
像这样的细节,其实片子里还不少,所以,我说这部片子算不上杰作,但绝对有资格成为一部佳作。
这样一个俗套简单的故事,在达内兄弟的讲诉下,像一团橡皮泥一样,有着各种变形和可塑性,一个下岗女工人的世界连接她周围人的世界,便在我们可见的,可说的的人物后面,隐藏了太多太多不可说不可见的东西了。
故,达内揭的只是一块纱,冰山下面的暗涌里裹挟了那么多与sandra发生关系的人物中幕后故事。
达内兄弟不会像好莱坞一样拍个续集又续集,也不会拍成超长电视剧,因为比起超级英雄,观众自然不愿意去看工厂工人的琐屑杂事啦。
4,最后一点,那个隐藏在背后的jean marc自始至终未出现,他的代理恐怕就是那个dumont,这是否借用了经典叙事中那个大佬在背后操控着台前的木偶演戏的情形,我不得而知。
但,恐怕那个jean marc先生就是冷静如斯的达内兄弟吧。。。
他们的风格不如其他大师那么突出和典型,但两天一夜,甚至之前的罗塞塔,单车少年的一脉相承或许就是他们的特质吧。。。
8 ) 不容易!
两天一夜 (2014)7.62014 / 比利时 意大利 法国 / 剧情 / 让-皮埃尔·达内 吕克·达内 / 玛丽昂·歌迪亚 法布里齐奥·隆吉奥内
我感觉当你遇到困难去求任何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有很会遇到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留住了你自己的决定。
要你来低声下气的,去求任何一个有可能保护工作的人,所以说我觉得这部电影反应的是女性坚强主义的电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推出每个人在生活中的不易,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知道!
9 ) 生活如此艰难,慢慢学会承担
拉选票避免被辞的故事。
同事中,有仗义善良的坚定支持者,有闭门不见的旧日好同事,有老实善良的同情者,有年少轻狂的反对者,有善良维诺的新人,有婚姻不顺的女同事,有家庭拮据的家庭顶梁柱。
最后的结果是8对8平,虽然最终难逃被辞的命运,却在这次事件中找到了信心,学会了坚强。
10 ) 《两天一夜》:故事就在这里,生活就是那样
达内兄弟的《两天一夜》讲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女主人公Sandra 是一间小公司的工作人员,因患有抑郁症而面临着被裁员的风险。
公司内部16名职工举行投票:裁掉女主人公或者加薪1000欧元。
在丈夫的鼓励下,Sandra 在两天一夜的时间里一一拜访这16名职员,劝说他们放弃加薪而选择让她留下来。
受限于两天一夜的时间,电影的叙事非常紧凑,很少有情绪表达的空间,即便有也停留在短短的几分钟内。
故事背景在电影开篇快速交代清楚,然后Sandra就开始了她的劝说之行。
中途失望过一次,又重新振作。
最后投票结果是8:8,Sandra没能超过一半的票数,她离开了公司。
有一个小插曲是:公司老板(或者经理)在最后提出让Sandra留下,这意味着另一位临时员工就不能续约面临失职,而这位员工在投票中是支持Sandra留下的。
于是Sandra选择自己离开。
从故事情节看,观众会以为这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情景剧。
里面有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有主人公个人心理历程的成长,有所谓的成败,还有小插曲。
以好莱坞式的模式,这会是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观众可以从中感受到正能量,Sandra的故事就是一个美国梦的缩写,可以说是“虽败犹荣”,甚至投票选择还可以投射出对于人性的争论。
但是别忘了,这是一部入围戛纳金棕榈的影片,它总有它的特别之处。
达内兄弟对于故事的讲述非常节制。
故事只有一个明显的悬念:投票结果。
而这个悬念足足拖了90分钟。
一方面,这反映出了编剧(亦是达内兄弟)编写故事的水准;另一方面这样的方式也挑战着观众的耐心。
观众需要同Sandra一同去感受一次又一次的拜访,一次又一次无奈的劝说,还有很多次的被拒绝。
但是,影片最值得提出的是,在90分钟的叙事时间里,可以说没有任何煽情的部分,也没有激烈情绪的出现。
对白很平常,没有励志的语言,也没有绝望的悲鸣。
在最失望的时候女主角甚至是没有对话的:女主角吃下了所有治疗抑郁症的药丸,然后躺下睡觉。
音乐的运用也非常节制,也减少了煽情的可能性。
印象中只有一处用了比较情绪化的音乐,而且不是背景声。
当Sandra同丈夫,同事一同开车回家时,他们都说到喜欢摇滚,开车的丈夫把音量调大,三个人跟着节奏唱了起来。
可是这个段落不到一分钟。
影片结尾,Sandra离开公司,走在一条公路上,然后摄影机停止不动,画面变黑,预示着影片结束。
没有背景音乐,最开始会以为电影此时没有使用任何音效,可后面又隐隐约约听到了公路上汽车开过的声音,这也成为影片真实感的表达方式。
而影片的拍摄也几乎是在室外,镜头的运动让观众觉得一直是处于自然光中,加上纪录片一般的拍摄手法:室外人物活动的跟拍,大量近景镜头,少有空镜头……都让电影有了很强的真实感。
因此,《两天一夜》虽然有了一个看似“精彩”的故事,结果效果却是“平淡”的。
但是,这种“平淡”却形成了这部电影非常吸引人的魅力,也是一种少见的“平淡感”。
当然,有很多电影都有一种“平淡感”的美学风格,像是亚洲的小津安二郎,贾樟柯,侯孝贤。
但在这些“ 平淡感”之后,总有一些导演个人的情怀想要传达,或者观众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愁”与“思”。
就个人观感而言,《两天一夜》并没有带来复杂的思绪,很难感受到其中主人公的励志情绪,低下阶级的生活苦恼,以及这个经融危机缩影下的故事的悲哀或讽刺。
《两天一夜》还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电影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
当我们看了那么多励志的故事,做了那么多梦,流过那么多眼泪,也有了那么多深邃的思考后,电影又意味着什么呢?
当我们已经熟悉励志故事的套路,知道电影这台造梦机的逻辑,明白流泪的原因,发现深邃思考(这些思考是伟大的影片带来的)后面其实只是另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反对主流的、现有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操作时,我们是否还会沉迷影像的魅力?
是不是还会心甘情愿地坐在黑暗的影院里看这台造梦机“千变万幻”的故事?
我们是不是还能对于这些已经熟悉的故事,情绪和情怀心有戚戚焉?
观众的审美风格会怎样走下去?
而电影又去怎样发展下去呢?
这是交给未来的问题。
这样的情况下,去评判一部电影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我们需要一些电影来激起我们的肾上腺素,我们也需要一些电影来满足我们在现实中无法获得的体验,我们还需要一些电影来帮助我们沉淀自己,思考问题。
当然,我们同样也需要一些电影像《两天一夜》一样,看完之后就像没有看一样的平淡。
无所谓中意与否,更无所谓好坏,观众需要的是它们的所有的寻在。
因为,故事就在这里,生活就是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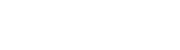























具有相當程度社會學樣本意義之影片:設計規則將裁員轉化為員工內部爭鬥的老闆,效勞於老闆的爪牙,看似接近了中產生活、但一旦失業就幾乎意味著致命的發達國家藍領勞工群體,影片對這三類人的刻畫皆堪稱精准。女主角必須在兩天一夜中,讓每名參與裁員投票的同事親眼見到她,親耳聽到她向他們訴說自己的境況和訴求,才能喚起同事基於樸素道德意識的幫助,影片對於“見到”的必要性的強調,頗具哲學意味。從結局看,女主角似乎是失敗了,但她卻說她覺得自己勝利了,這既因為她以自己的被裁保住了非裔臨時工的職位(這又是一個“見到”的故事),也因為她通過這一系列讓外界“見到”自己的行動,證實了自己作為社會中人的存在性。2022年5月28日14:00於百麗宮獵德4號廳,達內兄弟電影回顧展廣州站場次甲。
两天一夜,人性冷暖。人性都一样,与社会文明程度无关!收尾不好。歌莉娅女神形象全无,这牺牲!
看到个影评:“法国梅婷” 笑尿了… 这种二十分钟就能演完东西一定要拍成电影
@百老汇moma。1.与《无名女孩》一样,是对列维纳斯他者理论的另一次“面对面”的影像诠释。但《无名女孩》医生不断的寻访是出于一个形而上的动机,而《两天一夜》则是绝对形而下的:女主像罗塞塔一样,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更让人易于共情的是,不同于达内大部分电影里坚强到近乎偏执、不近人情的主角,本片的女主展现出令人心疼的脆弱(何况她还是玛丽昂!)。这比另一个罗塞塔可信多了。2.重复最考验编剧,而本片里每次不同的会面都牵连出轻重不同的戏剧性。一个人的困境与十六个人的困境交织,啮咬每一个犹豫是否支持女主的人的心。3.在最初的设想中,达内希望救了自杀女主的是《无名女孩》里的医生。达内宇宙差点成型。4.为我女神加颗星。
不厌其烦地挨个展示女主需要拜访的工友们,每一个拜访过程都要拍,可以一窥这一个阶层生活的样子,质朴的同时情绪调动上又非常有力度;马良的表演那种恰到好处的破碎和重压之下的坚强非常棒。我个人不大喜欢对女主抑郁症的处理,女主说丈夫对她已经没有爱只有同情,我倒觉得他丈夫更想要个家庭帮手,如果是刻意为之的话这个角度也很实际了。
只记得,那英老师当年就在CCTV天天讴歌下岗工人了
女神匈器缩水严重,差评
达内兄弟一贯的风格,中间一度觉得有些矫情,但是到最后越来越觉得活着对谁来说都是一场战斗,对于现在的许多欧洲人来说应该会很感同身受吧。
看的时候也在想。如果不记名投票的话 真的会不会为了奖金而投掉自己的同事呢,人性还是纠结的 一千块不多 那么如果是一万呢。 庆幸女主角反而可以因为经历这个事情而走出来活得更好。
看了很让人灰心
达内的故事主人公从社会最底层逐渐变为蓝领中产阶级,于是他们的困境更变得令人感同身受:失业、房贷、家庭,甚至抑郁症。有时候一个人眼前的选择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多,只有挣扎过才会自己看到光——还好,近两部都有很暖心的角色。歌迪亚真是太棒了,她鼓起勇气说出的话,声音都在颤抖
没有预想的好
就像一篇中规中矩的考场作文。没有感情的酝酿,没有细节的惊艳。这样的电影永远不会被我认可。
达内兄弟拍出了一种隐晦的难民题材片,民主选举只是途径,难民一定能留在欧洲。
你恐惧面对那些排挤你的人,可你又要怎么面对那些支持你的人?
好无聊
真的觉得好无聊啊…求人帮忙好歹也要请个客送个礼啊…还有,工会哪去了?
原来法国人也是很喜欢践踏草坪的……
啪啪啪~结尾响亮的耳光
#达内兄弟回顾展#打工人为了保住份工可以有多拼,剧情看似简单,甚至有点随意,但是导演的厉害之处就是能将这种生活流拍得引人入胜,并且能够利用十几个人物的几句对话带出整个社会底层现状,同时也能在重复中带出不同,塑造性格,镜头紧跟人物,甚至很多传统的反打位都没出现,空间控制得非常节制,这样也更能进去人物的内心,当然歌迪亚的表演也很成功,为数不多的车里的两段音乐这次也起到了推进剧情的作用,虽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团圆,可是我更喜欢这个结局,个人的选择影响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别人的命运,比起工作,更重要的是重燃生活的希望(当然这个“光明”的结尾也有点太不达内了,削弱了生活的力量)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