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时凶间》剧情介绍
郊外的一所大房子里,单身妈妈麦迪逊·海勒(艾丽·拉特 Ali Larter 饰)独自带着一双儿女雅各布(麦克斯·罗斯 Max Rose 饰)和海莉(科洛·佩林 Chloe Perrin 饰)过活。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她饱受惊吓,因为在寂静的夜里,她和孩子们都曾目睹一个可怕的怪物在房间内出现。恐怖事件愈演愈烈,孩子们的身心受到极大创伤,海勒家的生活乱作一团。期间她也曾找过相关组织调查,但对方被吓得落荒而逃。在绝望的时刻,她只能选择相信男朋友尼古拉(阿俊·古普塔 Arjun Gupta 饰)。 尼古拉利用高精尖的仪器调查,不曾想居然将怪物的实体召唤出来。海勒一家的噩梦远远没有结束,她们不得已被困在这个熟悉而又恐怖的家中……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北回归线黑鸟黑鸟黑莓魅力四射狂喜人民公仆第三季最后一个男人第一季初来乍到第二季萍水相腐檐廊下生活大爆炸第十一季精灵宝可梦:皮卡丘的心跳捉迷藏冠与锚内疚青之驱魔师:京都不净王篇蛇与毒超级战舰亲爱的她们梦华录甜蜜海风青天衙门2窒风之中第一季夜袭寡妇村黄阿丽:风流女子天佑吾王昨日我们还是孩子罗马尼亚制造银河护卫队3绿毛怪格林奇黄皮幽冢上帝的国度护士小姐歪小子斯科特对抗全世界
《航时凶间》长篇影评
1 ) 给那个给一分评分的人看
有时候看完电影,我习惯来看看影评,不过我看到有人给出一分还说出了很多本片很烂的证词,说这种行为很愚昧不值得宣扬,可我想说宗教并没有对错,他可以引人向善,也可以愚昧众人,但既然能一直存在,说明他有存在的道理,人们通过朝圣并不能带来更好的生活,但是心灵可以得到一定的力量和洗涤,就和很多徒步背包客或者骑行者一样,在大自然目前变得卑微,一切的痛苦在大自然面前,在巍峨的神山面前都显得那么渺小,在行走中抛开了一切杂念,让心灵得到放空,这是一场心灵的朝圣,只是方式各不相同而已。
而这样的朝圣是否真的有意义,我想每个人的起心动念不一样,或者理解不一样,结果也各不同,但既然每年有这么多人一直在坚持,至少说明大部分人通过这样的朝圣获得了心灵的升华和满足,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还说导演傻逼来宣扬这种题材的,我想说这只是一步纪录片,导演只是选取很小的一个角度去记录这个过程,从头到尾导演并没有说朝圣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改变,一切都非常自然毫不做作,并没有看到导演的个人主观的指引。
本片甚至没有加任何背景音乐,唯一的音乐就是人们的颂经词,还有人说算是导演摆拍,就算真是摆拍,那绝对水平也真是高,因为影片从头到尾我没有看到任何做作的成分,我感觉非常真实,至少作为纪录片而言,我觉得是很优秀的。
走过这条朝圣之路的人也行能更客观的评价这部影片,我走过,被这种精神感染过,我相信信仰的力量给精神的改变,我也承认生病的亲人是不能只靠菩萨保佑就能康复的,我只客观的谈这部影片的真诚度和客观性,没有看到任何主观的指引,所以我认为这部作品是五分的!
2 ) 这里所谓“信仰”是农奴制时期贵族喇嘛控制藏民的精神枷锁
有些人说这是信仰的力量,说这话的公知最多,他们嘴上说的纯净和向往都是废话,因为他们不会去也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最“纯净”的地方为信仰去操劳一辈子,他们只会把孩子送到欧美最世俗的地方接受科学教育,这就是公知们丑恶的嘴脸,他们一面言语上宣扬信仰的力量,一面行动上趋向最世俗的世界。
稍微学习历史的人都知道,藏区千百年来实行的农奴制,就是依靠所谓“信仰”这个精神枷锁来控制藏民,让他们不要反抗,把自己的劳动果实无条件奉献给贵族喇嘛去挥霍,维持贵族生活。
现在竟然把这说成是信仰的力量,我真是醉了。
我再抢到一遍,信仰自由有两个意思,第一是每个人拥有信仰一个宗教的自由,第二是每个人也拥有不信仰一个宗教的自由,而且选择是在充分了解这个宗教和这个社会以后做出的独立决定,这部电影里的孩子都是未成年,他们没有去充分见识现代文明,没有学过黑格尔和恩格斯,没有学过经济学和管理学,没有看过莎士比亚和爱因斯坦的作品,更没有了解藏区外的世界,在一个被人强行灌输一种思想的情况下做出这唯一的选择,竟然被人们加上一种神圣的光环,既然那么神圣,说这话的人自己怎么不从小就去干这个事情呢,当然他们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参与这份“神圣”,顶多去那旅游的时候把他们当作经典的一部分,仅此而已,回来就忘了,没有任何影响。
我从不是反宗教的人,我一直认为宗教也许是人类心灵的港湾,但前提是你经历社会和现实,你了解科学与感情,在拥有完整人格和判断,独立选择你的人生方向,那旁人无话可说,千万不要被唯美的图像和写意的镜头给忽悠了,看完发表那些经不住推敲的言语,忽视这个事实,事实就是残酷的精神枷锁还未解开
3 ) 值得观看的《冈仁波齐》
在成都买票看的,60座的影厅坐了九成,观众看得入戏,满意。
这样一部没有任何明星的纪录风格的文艺片,六天突破一千六百万票房,说明我们的市场和观众开始多元化了!
值得欣喜和赞扬!
导演采取了一种纪录-戏剧Docu-Drama的样式,让我们近距离地接近和感受了一次藏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实属可贵!
我在西藏拍过两部电影,知道张扬导演要花多大的力量、吃多少苦才能拍得这么好,这么深入。
从这点讲,怎么夸奖都是不过分的。
希望影院继续多排场次,希望观众们不要错过这部难得的电影精品。
4 ) 拍摄磕长头朝圣故事,算不算在消费猎奇心?
(原载蚂蜂窝专栏)电影《冈仁波齐》纪录/表演了一场从芒康经拉萨到冈仁波齐的超长距离朝圣之旅。
我分别用高德地图和谷歌地图查了一下两地之间有多远,要多久?
前者的“步行”选项显示,“步行路程过长,建议采用其他出行方式”,更改为“驾车”后,不停歇开的话,时间最短是35小时17分,2510.9公里,不过因道路封闭施工,而避开了片中大段表现的绝美318国道;后者不停歇的“步行“选项显示,23天19小时,2486公里。
电影中,也通过一个来自更远四川阿坝州的”路人甲“角色,界定了磕长头朝圣一天平均能前行的距离,10公里。
纳入大概2500总长距离考量,也就是得250天,加上片中角色们在拉萨停留两个月打工攒路费,以及等候产子、生病同路伙伴的康复时间,怎么都得一整年吧?
当然,文章开头用“纪录/表演“来描述导演张扬的电影表达方式,也就意味着这并非一部真正的纪录片。
在采访中,张扬说过《冈仁波齐》的拍摄大概一共九个多月,其中出发地芒康小村庄的日常生活,就拍了头两个月,而来自村庄4个家庭的11名”朝圣者/演员“们,更算是配合着拍摄来完成自己的拍摄,也就是大概每天磕一两公里路,积攒够素材,剩下时间搭车前行就可以。
这就从属性上,给带来这部电影带来第一个争议。
它究竟算剧情片还是纪录片?
虽然导演坦诚这是一个无剧本但有组织编排的剧情片,但那个作为上院线“准生证“的”龙标“却显示为”纪录片“。
很多年前在各种独立电影观影活动上,总会有刚接触了一些艺术电影的观众,在观看有些导演个人表达的地下纪录片时,勇敢站起批评,”你这样做是危险的!
“似乎非要捍卫纪录片镜头作为墙壁上苍蝇的伟大客观性。
我当时就实在纳闷,这有啥好危险的?
会伤及导演和观众的思想和生命?
后来,仿纪录片的剧情片或彻头彻尾的伪纪录片越来越多,进一步模糊了这两大类电影的界限,观众对此也越来越接受甚至非常欣赏。
具体回到《冈仁波齐》。
但芒康这11位藏族同胞们虔诚上路,一个四五分钟长镜头开始交待朝圣者该如何滑行般磕长头时,我不免开始担忧,这么下去会不会把人催眠睡着。
我看过其他表现藏区牧民真实生活状态的纪录片,比如季丹、沙青的《贡布的幸福生活》,即便清楚它的文献价值甚至深入真实的艺术价值,但实话实说,真在被拍摄对象挤奶、劈柴、喝酒、睡觉的日常中睡死了过去。
幸好,刻意或巧合安排的剧情,经过控制好节奏的巧妙剪辑,为枯燥的朝圣之旅带来了吸引人的故事——有孕妇中途阵痛,赶到县城医院生娃去了;最矫健的年轻人,被滑坡的山石砸伤了脚,而他家这一整年来诸事不顺;运载着帐篷和物资随队伍前行的拖拉机,中途被撞毁,只能变身人力拖车。
加上电脑壁纸般的蜿蜒公路、深山河谷等壮丽景色、拖车里婴儿视角看待朝圣大人们的特殊镜头,全程竟毫无睡意,且被队伍的遭遇和坚韧,激发起一丝感动。
当然这种感动可能是肤浅的,也远不止于产生吸引我入藏的冲动。
自己对藏区的兴趣一直有限,11年前进过藏区,并曾因突如其来的大雪封路,而在一个偏僻村子里被迫待了3天,言语不通的村民家给我吃了3天土豆、播了3天普通话对白的黄飞鸿。
虽然颇为感动,但也确信他们“在别处“的生活,与此刻也置身”别处“的自己太无关联,是一种咫尺天涯的距离。
导演张扬从以往作品中让观众熟悉的城市生活,来到藏区“在别处“的生活,拍摄完成的这部”走路片“(非公路片),也就不免产生引发争议的第二点——这2小时的时间,是不是以一种符号化的对信仰仪式的表达,去满足捏着手串的城市人对神秘异域的猎奇心?
至少在我看来,这种猎奇感无可规避,也不用太刻意规避。
欣赏德国电影大师荷索杰作《陆上行舟》,我们何尝不是对亚马逊雨林原住民和那个建造丛林剧院的疯子有猎奇心呢?
去年口碑爆棚的青海藏族导演万玛才旦作品《塔洛》开头,没读过书的牧民一字不拉背诵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又何尝不是展现一种独特的“奇观“?
而全片杜绝配乐的《冈仁波齐》,也在朝圣队伍即将抵达拉萨时,让大家跳起锅庄,谁又能说这是虚假的刻意安排还是磕长头队伍真就会这么休闲一下?
《冈仁波齐》当然远胜于那些浮光掠影的藏区航拍风光片。
从剧组角度,他们表现了信仰;从观众角度,我们消费了信仰;从朝圣者角度,他们拥有信仰,虽然其间的韧性和力量,远非电影艺术可以展现。
5 ) 以信仰的名义
在电影里,我看到的是一群目的极为明确的村民,他们的一切努力,承受的一切磨难都只为了一个目标,朝圣。
朝圣的确是他们的信仰,我尊重他们这个行为,但作为一个从小接受教育的人,我知道他们的朝圣只是徒劳,朝圣并不能改变真正他们的命运,实现他们的愿望。
然而最可悲的是,朝圣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已经是实现愿望的最终途径了。
人的一生,总有太多的未解之谜,过去是谁创造了人类,现在是谁创造了宇宙,终我们一生我们都找不到答案,所以我们只能自己给自己编造一个答案,因为有答案总比没答案好,哪怕这个答案是错的。
信仰和愚蠢并不冲突,他们的信仰遏制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想法,可悲的不是他们苦了一辈子,而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无数看客们都被他们的信仰所感动,但真正让他们去过那样的生活,去体验那样的灵魂之旅,又有多少人愿意呢?
6 ) 一锅新鲜伪信仰熬成的毒鸡汤正在靠近!
一分给本色出演的演员们,一分给影片漂亮的风景,信仰不是愚昧无知迷信的借口,更不是精神寄托,信仰应该是正面的,积极的,促使人强大坚定地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信仰党,就有了新中国,信仰雅典娜,所以星矢打不死,所有有正确信仰的人都有个共同点,不计较个人得失,甚至是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包括生命。
说回电影,看到有人评论导演想表达的是生活方式有好多种,没有对与错,那问题来了,如果朝圣算是信仰,那毫无意义就是他们的人生。
如果想表达的是信仰,可屠夫朝圣是因为杀生多了,为的是自己,我不信他回去不再杀生了,小女孩已经磕破头,妈妈却说继续磕,女孩子家磕头好,等等等等,每个人朝圣都带着自己的目的,和信仰无关,是他们自欺欺人的一个借口,谈何虔诚?
信仰不是宗教,喇嘛教更是伪佛教,把它渲染成信仰熬成鸡汤,不知道又该毒害多少人
7 ) 信仰
我要是说我看完电影不记得里面的人物名称,也不太记得剧情,甚至台词也没听懂一句,却看见了信仰,也不知道会不会被骂。
其实电影里面好像说的是藏语吧,反正就是没听懂一句,但是通过字幕还是能了解一点,他们是在讲信仰。
其实要说片子好不好看,这还真的不好说,你说我连台词都听不懂,我要是说好看,也无人会相信吧。
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这种有着特殊的地域文化的片子的,尤其是看到他们的信仰,我在想我的信仰是什么呢?
也许是那个被我当做明星一般的人,也许是他讲述的道理?总之我开始寻找我的信仰,那么你呢?
8 ) 各自的朝圣路
前段时间,在即刻视频拍的短片中,我回答了一个和电影有关的问题:怎样看经典电影?
我的回答是:三个“不怕”。
不要怕经典,不要怕剧透,不要怕自己的直觉。
不要怕经典,经典其实并不遥远,并不高深,一部电影能经过时间的筛选留下来,恰恰因为,它和我们有着密切关系,或者生活,或者心灵。
不要怕剧透。
一部电影,是不可能被剧透的,好电影尤其是这样,有多少次,我先看了最完整的剧本,都想不到最后拍出来的电影是什么样子。
剧透反而会帮助我们对一部电影了解更多。
不要怕自己的直觉。
专家说什么,影评人说什么,不重要,自己看到的,自己感受到的,就是最正确的,最珍贵的,也是对一部电影最好的回馈。
其实,这也适用于所有的电影。
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看,不要怕它影响到自己,不要怕自己的直觉“不对”。
对张杨导演的《冈仁波齐》,也是这样。
我想用它做样本,说说我是怎么看这种似乎很不简单的电影的。
▲《冈仁波齐》的导演张杨先生,他之前的作品有《爱情麻辣烫》《洗澡》《昨天》《落叶归根》《飞越老人院》。
这是一部用纪录片手法拍出来的故事片,但它的故事,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十一个藏族人,从芒康出发,走了两千多公里,去拉萨和冈仁波齐山朝圣的事。
听起来似乎很让人害怕,怕它沉闷,怕它乏味,怕它艰涩,怕它不够“好看”。
不用怕,它很好看。
先看故事和画面。
的确就是十一个藏族人朝圣的故事,这十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分别属于好几家人。
故事发生的这一年是2014年,是藏历马年。
▲出门朝圣前,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这是朝圣者用羊皮制作围裙。
在藏传佛教里,马年是释迦牟尼降生和成道的年份,也是冈仁波齐的本命年。
这一年里,诸神都会聚集到冈仁波齐。
平常年份,朝圣者来此转山一圈,可洗尽一生罪孽﹔转山十二圈可免地狱之苦,转108圈今生成佛﹔而在释迦牟尼诞生的马年转山一圈,则可增加一轮十二倍的功德,相当于常年的十三圈。
这十一个人,有老人,有孕妇,有屠夫,有残疾的小孩,他们就风尘仆仆地上路了。
一路上,他们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有人被山石砸伤,孕妇生了孩子,一路上,他们还不断遇到当地人和别的朝圣者。
▲在路上,朝圣者遇到了一家人,他们正在集全家之力盖房子。
最后,他们用了一年,到达了拉萨和冈仁波齐山,去了布达拉宫,也在冈仁波齐转了山。
所有的心愿都得以达成。
▲一步都不能少。
看起来很像纪录片,但看到一半,就会隐约觉得发现,它是有故事的,是对素材有过筛选和调停布置的,毕竟,一趟现实的朝圣路,未必恰好能发生那么多事,而一旦用电影来讲述朝圣,必须要对事件进行集中。
这种隐隐约约,似有还无的故事,我很喜欢。
这一年时间,他们走了两千公里,经历了四季,周围的环境一直在发生变化,雪山,草原,油菜花地,被桃花杏花围绕的小村庄,绿树招展的夏天。
▲电影中景色的变换,说明了他们朝圣所用的时间。
这些画面,我也很喜欢。
这都是我们未曾经历的生活,未曾经历的画面,本来完全可以用特别的光影技巧,拍得像油画,像明信片,本来完全可以极力放大。
但张杨导演,用过一种并不张扬的态度,拍下了这些画面,似乎不很在意,似乎漫不经心,这些画面,又美,又轻松,又不用力。
这种姿态,我也很喜欢。
再看信息量。
我常年生活在西部,我家距离甘南藏族自治州,只有三百公里,距离青海、四川和西藏,也并不很远,我也有很多藏族朋友,跟他们有很多来往。
所以,我一直想看到一些很踏实,很少抒情和编导介入的藏人生活记录,书,电影,都可以。
有丰富的生活细节,有生活气息,不装神弄鬼,不自我感动,只要有未经污染的信息就好。
尤其是对朝圣,我更是充满好奇,那些朝圣的人,都从哪里来,他们这样走一趟,要做什么准备,要经历什么,会不会得关节炎。
《冈仁波齐》用庞大的信息量,满足了我所有的好奇心。
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细节。
出发前,他们恰好在过藏历新年,大家忙忙碌碌地准备新年要用的东西,在客厅里挂出收藏的唐卡。
新年那天,聚在一起庆祝,还会互相串门。
▲过藏历新年,也需要准备很多吃食。
即将出发前,他们砍木头做护手板,到集市上去买胶鞋,我也由此知道了,在芒康,一双胶鞋的零售价是45块钱,如果买得多,算批发价,就是35块钱,他们一次买了十二双,到了拉萨,他们又买了一次鞋,这次便宜点,批发价是30块,他们买了二十双,一共600块。
在路上,他们多半是吃肉,用小刀切下来,分给大家。
为什么不吃蔬菜?
因为蔬菜很贵。
一般不会住旅店,事实上,这一路也没有那么多旅店。
他们都是搭帐篷居住,每到黄昏,遇到比较平坦的地块,他们就开始搭帐篷了,男人一个帐篷,女人一个帐篷。
电影里有搭帐篷的全部过程。
他们用一辆手扶拖拉机,拉了所有的生活用品,包括搭帐篷用的东西。
快到拉萨的时候,他们的拖拉机被一辆面包车撞了,车坏了,他们只好丢掉车头,由男人拉着车厢继续前进。
▲男人们很自然地担当起一路上最辛苦的工作。
路上不能有任何投机取巧,晴天,就在晴天行走和磕长头,雪天,就在雪地里行走和磕长头,遇到水洼,如果是绕不过去的,就在水洼里磕长头。
车坏了以后,情况变了,男人们拉着车厢先走个几百米之后,把车厢放下,折返,回到起步的地方,磕着长头走到放车厢的地方,再拉着走几百米,再回到起步的地方,继续磕头。
总之,不能漏掉一步。
▲无论下雨下雪,都不能停止磕长头。
老人是团队里最受尊敬的,他们主持每天的聊天,祈祷,解答年轻人的困惑,睡在帐篷里比较好的位置。
他们是没有头衔的神职人员和心灵导师、调解师、气象观察员(因为他们经历过足够多的气象周期)。
▲老人是朝圣队伍的灵魂。
杨培老人手持转经轮,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故事并不复杂,加上张杨导演用的是纪录片的手法,人物永远在中景和远景的位置上,有一种淡漠和疏离的感觉。
但信息量并没有减少,这些信息,就藏在所有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里。
能够看到这些,我心满意足。
往深一点,还可以有深层的联想。
看《冈仁波齐》的时候,我想起的,却是福克纳的小说《我弥留之际》。
▲福克纳《我弥留之际》的封面,李文俊先生翻译。
小说主人公是农妇艾迪·本德伦,她有丈夫,也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是家庭的核心。
故事从她的去世开始,弥留之际,她要求丈夫安斯把她的尸体运回到杰弗生,和娘家人安葬在一起。
杰弗生并不远,就在四十英里之外,但这趟路,她的家人却走了十天,经历了重重磨难,他们遇到了洪水,洪水差点冲走棺材,拉车的骡子被淹死,他们抵押了财产才得以继续前行。
最终,大儿子失去一条腿,二儿子疯了,三儿子失去了辛苦工作买来的马,女儿被药店伙计诱奸,艾迪·本德伦的丈夫本德伦先生遇到了一个女人,娶了她当新太太。
《我弥留之际》,用这样一趟返乡之旅,映射的是整个人类苦难重重的生活。
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结尾之一:“他们在苦熬”。
▲电影《我弥留之际》,詹姆斯·弗兰克编剧、导演、主演。
2013年上映。
《冈仁波齐》拍的是朝圣,其实也可以看做是对人们生活的映射。
张杨导演,显然是想用这样一支小小的朝圣队伍,来容纳尽可能多的人生样貌,尽可能多的生活形态。
他在影片开拍前,有这样的要求:“首先要有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她)可能会死在路上;要有个孕妇,她的小孩会在路上出生;还要有个屠夫,因为杀生过多想通过朝圣赎罪;要有个七八岁的孩子,这样会增加很多趣味性和不确定性;有孩子就要有他(她)的父母;还要有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他可能是个小流氓,也可能就是一个青春期敏感害羞的男孩,一路上他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还要有一个50来岁、成熟稳健、类似于掌舵者身份的一个人,他会是整个朝圣队伍的头领。
”
▲《冈仁波齐》人物海报。
他们在朝圣过程中遇到的所有事,出生,死亡,受伤,不厌其烦地扎帐篷,100万次匍匐,每天的聊天和祈祷,其实也是人类都会遇到的事。
在预告片里,老人对女儿说:“磕头好,磕头长见识。
”也是因为,朝圣磕头,其实就是经历浓缩的人生。
拍摄团队的经历,也像是一次朝圣,从2013年11月到2014年11月底,拍摄团队一整年都待在高原,朝圣的人经历什么,他们也会经历什么,许多拍摄地,都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方,缺氧,寒冷,他们都要一一经历。
在《冈仁波齐》的幕后花絮里,我对这一切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演员是怎么选出来的,有着什么样的设定,承载着什么样的任务,在拍摄过程中,所有人又经历了什么。
▲ 张杨团队的工作照。
朝圣、磕长头,是苦行,苦修,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又何尝不是苦行苦修呢。
每天高峰期挤地铁,每天四五个小时的通勤,加班,耗尽全家所有积蓄、借遍亲朋好友的钱来买房,为了让孩子进入好学校,变成行贿高手,又何尝不像是在磕长头。
就像《冈仁波齐》的幕后花絮里说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是完全正确的……神山圣湖并不是重点,接受平凡的自我,但不放弃理想和信仰,热爱生活,我们都在路上。
”信仰,生活,爱,可能是一件事物的三个名字,是一个事物的三个面相。
其实,你我都有各自的冈仁波齐。
9 ) 冈仁波齐,神圣即日常 | 张杨专访
“我们念经吧。
” 这句话许多次地出现在这部电影里,不论是在普拉村每一家人的屋宅之中,还是在一千多公里的朝圣路上。
对许多都市人来说,禅修、念经、打坐、吃斋,做瑜伽,成为了逃离快节奏日常生活的一剂灵药,然而同一套看似相同的语词,在藏人那里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行为属性——因这一切仅仅只是日常,他们日复一日的重复,没有额外的选择,他们的生活之简单甚至简陋到,楼宇中的你不会真正愿意去亲身触碰。
当我们曾经在明信片或电视荧屏上欣赏到冈仁波齐的景色时,定会感叹青藏高原的神秘旷美,曾几何时那就像吹入双眼的一股清风,也许真能比中央空调所制造的冷气更多那么一丁点儿关于世界的幻想。
可是,自然地理的实存,以强大的方式支配并决定了藏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世代居住并臣服于巨大的沟渠与难越的险峰,在这种时空维度内的安身立命,其实是当代都市人概念中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真实界。
念经是一种几近沉默的自我对话方式,影片中的对话非常少,日常话语的内容也非常简单,念经几乎成了他们每天发声最多的部分。
每重复一次经文,每数动一颗珠子,都是用来与青藏高原独特的生存条件所相容相洽的方式,他们不需要同自然争论,只需在经文的护佑中让自己安于这片土地。
宗教在这种语境下,其实已进入到日复一日捏糌粑的过程中,日复一日砍木柴的过程中,进入到路途中无数个叠起的尼玛石,进入到不断交替袭来的苦难与快乐,进入到每个人都不能逃脱的生与死的过程里。
“我们念经吧”,它不是一个特殊的仪式、一个偶然的选择,它与那令人摒息的地理环境一样,成为了数万个生命举动背后那唯一的意义。
张杨最值得尊敬的地方,就是在《冈仁波齐》中,将藏人的这种日常生活细节提升到“神圣显示屏”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影片中大量描绘朝圣之前的生活段落中得以窥见,普拉村4个家庭的12个人物,一位寄希望于来世的老人、一位随时可能分娩的孕妇、一个想赎罪的屠夫、一个纯真坚韧的小女孩、一个想了却舅舅心愿的中年掌舵人……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命运走向就是讲故事的人希望抓到的一切,这也是这个电影几乎不需要剧本的原因。
影片的开头,张杨花了大量笔墨拍摄村里的日常生活,砍柴、做饭、缝补,在这些日常之后,似乎随着即将到来的朝圣之事而加入了一些更多的环节:去批发买鞋、砍制手板、制作糌粑,缝制牛皮围裙,冬季的村落忙碌起来,在袅袅的炊烟蒸汽、气息浓郁的青稞酥油、被擦拭干净的铜质器皿和厚软的毛皮织物间,一个流动而紧实的普拉村大家庭以一种全然真实的动态,近距离展现在我们的感觉系统面前。
张杨被这些极易被奇观观看者忽视的日常细节迷住了,他曾经甚至有过一个想法,就留在那个村子里,只拍摄这些藏人的日常生活,这个村子的一年四季,完全可以不需要“上路”,也能拍出一部好电影。
但这些“真实的演员”,这一次,命运还是驱使着他们和张杨的剧组一起走上了朝圣之路。
在整个故事中,没有一个区别于其他人的主角存在,所有人都是主角,这些朝圣者每个人各自遇到的问题其实是所有人的问题,群像不是缺乏重点,群像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一”,12个人的命运,生老病死,除了老人最后的死是导演虚构的设置外,其他几乎都是真实的自动呈现。
而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真事,完全契应了张杨最早的设想,那位孕妇出发没多久就分娩了,剧组拍摄到了整个生产的全过程,而这个婴孩丁孜登达,也可能成为了电影史上最年轻的演员。
生孩子、腿受伤、车头被撞坏,遭遇雨雪,都不会让他们折返放弃,他们只需稍作休整便能继续上路,在磕长头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不同问题,“磕头长见识”,而他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几乎都是在朝圣路上时常发生的事,没有预设,也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捷径,这些困难,最后对他们来说被转化了,困难不再是困难,而成为了加持朝圣之路的美好的经历,在齐心将其度过的过程中。
影片中出现过几次轻盈而精巧的情绪释放,比如车坏了之后,男人们辛苦地拉着半截车上坡,然后再折返重新磕头,以此重复,看得观众心里都揪了起来,不忍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倒霉”那么“苦”,不过,他们在上坡拉车的过程中,共同唱起了一首歌,越唱越有力气,越唱笑得越开,直到到达下坡段时,他们像小男孩一样欢呼地顺着破车乘风而下。
另一巧妙的段落是众人遇到大水塘时的那场戏,见汽车驶过所溅起的水花,他们脱了外衣,磕着长头淌水而过,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乐坏了,这严肃的磕长头在这一看似障碍的环境中闪射出这些藏人的勇气、轻松与纯真,以及隐藏着的一个深刻却简单的道理——很多困难,你以为是要命的大河,不敢触碰,其实你去经历去直面了就知道,原来它只不过是一滩小水洼。
这种在戏剧阵势上起伏极小但在心理释放度上却极高的处理,实则难能可贵,张杨深谙从最简单的生活细节中提炼诗意和哲理,朝圣作为一条道路(path),它最终要通向某处,佛法有“烦恼即菩提”,我们要找的东西,不在别处,就在我们鼻尖处的日常尘世。
回到影片中的一幕,朝圣者们的帐篷在大雪中,似乎正与冈仁波齐山神貌相合。
张杨专访Q:在《冈仁波齐》的朝圣队伍中,有一位屠夫,在您同期拍摄的另一部电影《皮绳上的魂》中,主角是一个猎人,他们都与某种杀生的形象有关,您为什么会对这一形象感兴趣?
A:屠夫在西藏的牧区是一种常态,《皮绳》里的那些演员的父辈一代几乎都打猎,每家人都要吃牛吃羊,需要去杀,只不过每一家只选一人去做这件事,比如父亲去杀,母亲和孩子就不碰了,因为藏人对杀生还是十分敬畏的,他们会通过念经或一些仪式去不断地为这种生存方式进行赎罪。
在《冈仁波齐》中,每个人的个人身份、家庭关系都是真实的,这个屠夫在村里地位不高,他的妻子虽然容貌姣好,但家里是瘸腿的弟弟主持,所以他也想通过朝圣,一方面进行自我的赎罪,一方面也想借此提高一下自己的地位,而且通过这一次朝圣,他还能挣回点钱来,这些都会给他带来非常具象的改变。
Q:电影中孕妇分娩的段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电影剧组是如何找到她并与她的家庭沟通的?
A:其实生孩子这件事,在朝圣路上不是特例,而是比较常态的事,我之前在路上看过到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就这样睡在拖拉机上,四个月大,牛皮包着,于是我们相视而笑,这就是我想要的。
然后到了普拉村,居然正巧有一个孕妇,我就跟她聊了聊,表达我们随队会提供一些医疗方面的保护,这对夫妻也很理解我们,觉得是件好事,后来问她怀孕几个月了,她说不知道,她们根本弄不清,我们上路之前,带她去医院做了个B超,其实那会儿已经8个月了,后来出发没多久,一天晚上就分娩了。
Q:片中唯一的虚构情节——老人的去世,是路上临时决定的还是之前就确立好的?
A:其实在找到普拉村之前,我最早就这么构想的,一生一死,这个结构是必须要有的。
这些人物后来都在这个村子里找到了,特别巧。
其实之前也有多种可能性的考虑,比如是不是要有一个主人公,但最后反复思量还是没往那个地方走,因为一旦有主人公了,你就要用劲,你就好像非要在他身上发生些什么事情了,就要编了,编的太多,我就觉得不好。
Q:您拍摄了非常多的朝圣队伍在上路之前的日常生活,有什么独特的用意?
A:这也是电影里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分,最早的版本里,这部分内容其实有近50分钟之长,就是普拉村里冬天的日常,藏历新年、赛马、上山砍柴等等,某种意义上我喜欢这样日常的状态。
我当时曾经还有过一个想法,在那儿待了两个月后,我和摄影师说:“也许咱们不用上路,不用去拍朝圣了,咱们就村里待上一年,就慢慢看春夏秋冬,看这个村子里的人的变化,肯定也能拍出好电影”,当你安静地观察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意思的不是戏剧性的大起大合,其实就是日常的四季变化,通过这样一个村子,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生宽慰的东西。
所以我想在整部片子里尽量多地展现村子里的日常。
哪怕上路了,磕头也已经很仪式化了,我们还是要回到日常,藏人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都是简单的事情重复重复重复,上路朝圣之后,最终还是要回到日常。
这是整个电影一个最基础的态度。
当然或多或少,作为导演我也很清楚,里面偶尔还是要在对的地方加入一些戏剧的东西,做得紧张一点,小的高潮的段落,但只能是相对性的,不能用力太大。
Q:影片中露出过几次现代生活的银色瞬间:村里的晚上忽然来电了,电灯亮了,原来他们村里是有电的;一辆现代的汽车撞坏朝圣者的车;快接近拉萨时,朝圣者们用一台银色山寨苹果手机给家里打去电话。
就您跟藏人多年的相处生活经验,您觉得他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是怎样的?
A:你说的这些影片中的瞬间,其实也来源于我们实际的观察,尤其住在他们村子里的时候,感触很深,其实现代的东西他们都有,手机、电视、太阳能,但我们发现藏人基本不看电视,手机每家是会有一个,但用的比较少,直到今年,晋美才学会用微信传照片给我,之前完全不会,手机主要就是用来打电话。
你会觉得,虽然有了这些现代工具,但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半牧半农的,多少个世纪以来没什么变化,他们自给自足,物质上会有需求,但没有什么过强的欲望。
片中有一家我记得后来还真背回去一个洗衣机,他觉得洗衣机好像是需要的,还有生小孩的这一家,父亲回去后想做一个旅店,就在318公路边的村口那儿,几个床位的那种,因为他们在路上的经历打开了一些眼界,回来后思维上会有一些变化。
Q:这群素人演员在拍摄过程中给留下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A:他们有过两次停滞,就是觉得好像不能拍了。
特别是在拉萨那场戏,他们在布达拉宫边上磕头,之前一路上他们也习惯了拍电影的那种一次两次重复拍的模式,但在布宫那次拍到第三遍,他们突然不干了,因为旁边的藏民吐他们唾沫,他们逆时针往回走了,其他人就觉得他们犯了忌讳,他们内心感觉受到了侮辱,那天后来咱们就不拍了,回去休息聊天了。
在那一刻,他们在演真实的自己,所以那唾沫真的是吐在自己的心上,这造成了一种身份的冲突,而职业演员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后来生小孩的一家的舅舅是小昭寺的喇嘛,喇嘛劝他们:“你们可能没意识到你们其实在做一件非常好的事”,他们才放下这种焦虑。
Q:你觉得汉族导演拍西藏和藏族导演拍西藏有什么区别?
A:藏族导演怎么拍都对,汉族就有可能会不对,角度、分寸就变得很重要,猎奇的东西我们坚决不要,你必须深入到真实的里面去,你才敢拍,你连这个都做不到,说实话你根本就不敢拍,对一个民族、一个宗教、一个地域如果只是浮光掠影的话,是根本不行的。
Q:20年前您在拍《洗澡》的时候就已经展露了对西藏的某种情节,到如今拍完《冈仁波齐》,你觉得在这个跨度里,西藏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A:这么说吧——西藏,它总是勾着你。
前面去过那几次,你心里就知道,你会再去的,如果你是个作家、一个音乐家的话,你的笔触当时可能就已经流出来东西了,但一个电影导演,心里暗暗知道,早晚有一个电影会诞生出来。
Q:您以后的创作会只专注于西藏题材么?
是否会回归都市类电影?
A:像《向日葵》《洗澡》这类都市题材的电影,我还是会去做,因为这还是我真实生活的一部分,目前这个阶段,只是把你灵魂里的(西藏)这一部分呈现出来,人总是在不同时期会触及到不同部分。
Q:非常期待,也让我们觉得难得可贵的是,您在创作和体验上的无分别心,在某一种特定的形式中可以关照到普遍的问题。
A:《冈仁波齐》其实曾经还剪过另外一个版本,结尾的冈仁波齐天葬台,镜头一切,回到普拉村,清晨,和影片的开头几乎是重复的,尼玛扎堆点酥油灯,念经,斯朗卓嘎几个人把牦牛牵出来,然后上山砍柴。
这可能是我觉得真正的“回到日常,回到世俗”的结尾,其实关键就在于,在日常和神圣之间,你怎么去建立这个桥梁。
10 ) 信仰是什么?
信仰是什么?
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生活中,我经历的许多道德低下,甚至败坏的人,屋子里都供着金光闪烁的藏传佛像,他们干着那么多寡廉鲜耻,甚至是生灵涂炭的事,还要找有信仰的感觉,于是很多人开始表演有信仰。
平凡人不知信仰为何物,在迷茫的生活中,苦苦求索,这很正常,也并不可怜,但是明明没有信仰,或者不知信仰为何物,却要信誓旦旦地表演信仰就是很无聊,又可耻的事情了。
六千多万票房,意味着有二百万观众看了这个电影?
都在这片里找到了信仰的力量了?
我,不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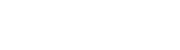


































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怀着近乎猎奇的心态,以他者的视角观看他们时,一边难以遏制感动,一边感到陷入某种罪恶的困境,警惕被唤起的哀怜情绪,也不想将他人的日常、文化与信仰奇观化。
变成风光片有点可惜,心灵美多展现点就好了
记录真实,情景重现
去时间化,去标签化,虚无与信仰,公路片永恒不变的主题。
這是一條純粹的朝聖之路,不需要太多的修飾,就靜靜的陪著他們一直走向自己渴望的終點,人一定要有信仰
不给一星,就无以表达我的愤慨。几个观点: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2如果我是导演 会强烈的批判和嘲讽 3有生命的不仅仅猪牛羊 植物也是生命 4什么时候才能有像我滴个神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片子 5多么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地区 有信和不信的自由
我在藏地生活过几个月,知道这是我不能碰触的题材。很多观众觉得导演在卖信仰,批判朝拜是种愚昧的行为,而这些批判者大多数是在大都市,挤着地铁过着朝九晚五生活,忙着工作愁着买房,以为这是生活的全部。被现代化与智能科技让自己忘了什么是信仰,更不知道信仰的力量有多大。而我不迷信,但我有信仰
无上的信仰 唉 理解不能哟
一味的朝圣,却从不思考朝圣的意义。盲目的信佛,却不愿意做实事来获得幸福生活。磕长头到西藏就真比上班更高尚?和《偶滴神啊》《我的个神啊》相比太浅薄了。
208赞排名第一打了一星的短评真的low 不尊重别人的信仰和文化 并且用狭隘片面的观点去加以评判
不好这口
信仰放大了精神的意义,也会阻隔物质的价值。
首先有无信仰和电影的好坏并无关系,张扬用伪纪录片手法全程摆拍的朝圣路,这没什么问题,但使劲儿用信徒的虔诚当成自己创作的真诚这种自我麻痹的心态换来的只有过度消费这片土地,就和强行选定的冈仁波齐这个片名一样,张扬只是把神山当成了路的终点,可在信徒的眼中,冈仁波齐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想起了塔尔贝拉的《都灵之马》,想起了尼采的都灵之马。不是滋味儿。对啊,是什么样的神明,需要生灵这么苦?《都灵之马》是上帝已死的“重复”,《冈仁波齐》是坚信佛陀在世的“重复”,但两者,真没有什么不同啊。
电影是好电影。别人的生活理想也应该被尊重。就是觉得如果他们把这种精神和付出,用来送快递送外卖开滴滴,或许早已经得到了神所不能赐予的幸福和安乐
虽然这不是我所感兴趣的领域,有宗教有信仰也好还是无神论也好,我对这些不做评价,更何况我也没资格对别人的信仰做评价,但他们对自己信仰的虔诚使我敬畏
这部电影或许带来了这样一种通识幻觉:银幕前观看的人强行与银幕里的人达成两小时的隐形契约,以此换取一份跳出生活经验之外的自鉴履历。
对于「朝圣之旅」如同白描一般纯记录的手法,试图将风景与解读一股脑儿丢给观众,是一种看似客观实则肤浅的态度,最终只是一个看客的「旅游路人」视角。
一般,对信仰的处理可以说非常冷静克制了,可也缺乏可看性和层次感,单纯的纪录片都可以比这个更有意思。去西藏的寺庙里头的时候真的能感觉到那种厚重的信仰,不敢造次。
这么好的题材,应该可以处理得更有思考一些吧,虽然在大银幕看一场朝圣还真是蛮特别。作为一部伪纪录片,镜头背后的故事说不定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