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情介绍
2019年5月,几十位作家来到山西汾阳的一个小村庄,他们在这里谈论乡村与城市,文学与现实。影片以此为序曲,交响乐般地以18个章节讲述出1949年以来的中国往事。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三位作家贾平凹、余华和梁鸿成为影片最重要的叙述者,他们与已故作家马烽的女儿一起,重新注视了社会变迁中的个人与家庭,让影片成为一部跨度长达70年的中国心灵史。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辰雪令艺术窃贼风流才子翻转天鼠来宝3失落的海峡女浩克风城大佬第二季寻找恋人的方法烈日灼心凡妮莎海辛第四季觅踪寻迹无线伪装者海贼王特别篇:黄金之心触摸冤家成双对第四季梅森探案集第一季破晓走过冬季破碎的瞬间全息游戏:恋爱世界玄笔录前传之怨妖坛地狱客栈:试播集偷心大圣P.S.男AI崩坏幸福是一条温暖的毛毯法兰西大师狄仁杰之骷髅将军亡灵召唤花豹少女队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长篇影评
1 ) 关于游泳
在不同时间去回忆几十年前的故事,可能引发表述当下产生的情绪和情感是不同的。
何况是面对有意的拍摄。
如果看见这种困难,电影本身也好,观众也好,若想要挖掘出时空变化,人世变幻的真实,那可能是一种徒劳。
因为结构主义大概会说,一旦去表述它,可能就因此失真了。
何况电影章节还是碎片式的,但是有意义是通过对人,特别是口述者以外的人的一个个特写在倾泻这种力量。
你只要有些感动,甚至感伤就好。
猜想和贾导年龄相仿的人可能完成在电影里与贾导一致的某些通感。
还能看出电影章节的承里其实掺杂一个当代青年想象中的乡土作为符号的味道,有意的在寻找乡土之为这些文学家摇篮的关系,可惜它们因为没有经历过无奈的饥饿,不能体会那种野蛮之力,当用过于温饱之力显得表现力反而勉强。
其余,任何想从电影归纳意义,或者想被影像方式,能整体的从乡土,文学,个人成功等符号析出超越于片段的精神的话,那恐怕曲解了电影作用。
所以,对电影名字的揭示是在最后一帧才出来。
靠近岸边的水都是黄色的,要看到真正的海水颜色,那就要一直游,直到海水变蓝。
好像是说,岸边的人啊,要懂得什么是蓝,那就去游吧。
虽说用游泳这个类比人生几十年未必恰当,话说谁不都是在时代的海水中浮沉。
然而,只有很少的人在为了什么而去游泳,有些凡人实际自己也不用游,漂着不死去也是一种故事了,毕竟海水会推着人走,所以只能相信海水的天蓝,把身处在蓝色海面上当成一种奇迹或偶然。
2 )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札记
劳动使他高于地面,但工具比他更高。
高举着锄头,犹如高举着劳动的旗帜——于坚 《想象中的锄地者》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
——沈从文 《致张兆和情书》我觉得乡村就是现实——韩东写诗不要把自己生活也诗化了——贾平凹书上说:你生在那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乡也叫血地。
——贾平凹 《带灯》白眼观世——贾平凹死亡是凉爽的夜晚,生命是闷热的白天。
——海涅《还乡曲》回首往事或者怀念故乡,其实只是在现实里不知所措以后的故作镇静,即使有某种情感伴随着出现,也不过是装饰而已。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父亲一直是我的疑问。
而所有疑问中最大的疑问就是他的白衬衫。
那时候,吴镇通往梁庄的老公路还丰满平整,两旁是挺拔粗大的白杨树,父亲正从吴镇往家赶,我要去镇上上学,我们就在这路上相遇了。
他朝我笑着,惊喜地说,咦,长这么大啦。
在遮天蔽日的绿荫下,父亲的白衬衫干净体面,柔软妥帖,闪闪发光。
我被那光闪得睁不开眼。
其实,我是被泪水迷糊了双眼。
在我心中,父亲和别人太不一样,我既因此崇拜他,又因此充满痛苦。
父亲是怎么竭力省出一点钱来,去买这样一件颇为昂贵的不实用的奢侈品?
他怎么能长年保持白衬衫一尘不染?
他是一个农民,他要锄地撒种拔草翻秧,要搬砖扛泥打麦,哪一样植物的汁液都是吸附高手,一旦沾到衣服上,很难洗掉,哪一种劳作都要出汗,都会使白衬衫变黄。
他的白衬衫洁净整齐。
梁庄的路是泥泞的,梁庄的房屋是泥瓦房,梁庄的风黄沙漫天。
他的白衬衫散发着耀眼的光。
他带着这道光走过去,不知道遭受了多少嘲笑和鄙夷。
——梁鸿《父亲的白衬衫》《在乡村》那个傍晚,雨一直落到麦田里。
辽阔的麦田,辽阔的雨声。
麦子,植物,生长不易察觉,大地上的生命无不如此。
田野中的三株榆树陷入沉默,如同父亲、母亲和孩子。
雨也落进附近岑寂的村庄。
瓦片上,窗台上雨声迭响。
若屋中有人,他必记挂着麦田,拉开15瓦的电灯,不动。
而山岗上的灰山雀缩起肩膀,在雨中自学起有关寂寞的知识。
一列货车驶入隧道汽笛长鸣,仿佛一只困兽在黑暗中向前摸索。
等它开进真正的黑夜,四面是田野,没有星光,没有月光,雨也落在它苍黑的背脊上。
——西川《在乡村》伯恩斯坦指挥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1855年勃拉姆斯在故乡汉堡聆听了舒曼的《曼弗雷德》戏剧配乐后,内心勃发了极强的创作欲望,他立刻构想谱写这部交响曲章节:一:吃饭二:恋爱三:马烽四:回乡五:新与旧六:声音七:远行八:贾平凹九:病十:余华十一:活着十二:梁鸿十三:母亲十四:父亲十五:姐姐十六:收获十七:儿子十八:游泳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一种认为自己是汾阳人的错觉。
确实,贾家庄正是中国乡镇的缩影沉浸在长焦的快感中余华的爱情故事好有趣啊哈哈哈哈!!!
3 ) 贾平凹:你生那里其实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乡也叫血地 余华:我要一直游,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文/Somer(子非鱼)
没有中文版,手动加一个看完电影回到家,已经是柏林时间晚上七点。
打开手机微信,发现自己漏掉一条上午的重要信息,在乡下外婆家的舅舅发来信息说:“现在可以打过来(微信电话),外公在门口等你。
”外公和外婆住在湖北乡下,距离武汉只有大约两小时自驾车程的距离,今早,作为乡村医生的外公接诊了外来人员,舅舅说外公在家自行隔离。
我们的视频计划必须推迟。
谁知,住在湖北乡下的外公外婆为了看到我一眼,特地跑到了隔壁舅舅的屋子门口,等著和很久没见的外孙女说说话。
就像贾樟柯在电影开始前说的最后一段话:“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中国人最困难的时候,在出发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按时抵达柏林。
最后,我们还是来了。
我想,这个时候,电影应该存在。
”对于当下身在国内的人来说,看电影、逛街、聚会之类的活动都是加速病毒传播的危险行为。
人们只能在家里等待,等待“禁足令”的解除。
我不敢写太多“春暖花开”的希望风格的句子,这场持久的抗疫战中,我并没有做什么。
这部电影以前的名字《一个村庄的文学》,不知道是不是“改编”刘亮程散文集的名字《一个人的村庄》60后作家“代表”余华从小生活在浙江海盐,一个靠海的小城,小时候,他和小伙伴们经常去海里游泳。
那时候,海盐的海水是黄色的。
在学校上课时,课本里说海水是蓝色的,他经常想:为什么我都看不到蓝色呢?
有一天,他游了很长一段距离,一边游一边想着:我要一直游,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酷酷的60后余华夜晚的海盐,他走在海边,说着自己儿时的心愿。
影片在这里画上句点。
这时,我旁边的一位德国奶奶说了句:“Toll!”(太棒了!
)而我想到自己小时候读完课文后冒出的疑问和与余华相似的渴盼——山的那边是海吗?
在被小山丘环绕的我家乡的小镇之外,可以看到大海吗?
作为一部以作家为主要受访者的纪录片,这是一个很好的开放式结尾,有充分留白,也让人感受到这些作家各自探索自身出路时的诚挚和坚韧。
最后一个提问的年轻人直接引用影片的片段,并抛出一个“导演可能觉得有点难回答”的问题:影片里有个片段,余华的短篇小说被《北京文学》选中后,编辑叫他去北京改稿,原因是“这篇稿子的结尾太灰暗了,在新中国绝对没有这么灰暗的事情,得改一个光明的结尾,稿子才能发表。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场景可能有点讽刺。
不过,在影片结尾的合作方和感谢名单里,我发现很多政府机构的名单。
而结尾的“游到海水变蓝”也有种光明的结尾的感觉。
我想问,贾导有没有收到编辑的要求,所以特地给片子设计了一个比较光明的结尾呢?
贾导对这一“困难”问题的回答很有力,他一步步拆开来回应。
他说,在中国,要拍任何地方,无论一个镇、一条街还是一个社区,你都得先申请拍摄许可,获得管理这一区域相关部门的批准后才能开机。
我想,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
另外,“我没有一个像余华当时那样的编辑,这部片子的主要投资人是我自己,我没有提出这样要求的’编辑’,没有特地做一个“光明的结尾”。
”最后,作为某种对提问和对电影开场时候那段话的“呼应”,贾导也引用了余华作为他这部电影全球首映的结尾。
“我想,无论是电影工作者,还是别的领域的人,都会有一定的希望社会变好的理想。
我拍电影22年了,拍到现在,我发现,期待的改变其实很缓慢,当然有某种疲惫,某种失望。
但是,在拍摄这部记录片的过程中,听贾平凹讲他的经历(文革时,作为镇上教师父亲被批为国民党特务分子,撤销公职,被押送回乡下老家,父子俩见面时,贾平凹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哭泣......),到余华的经历(全场观众几次的笑声都被余华这部分包了),再到梁鸿用她的文字,讲述她自身以及这个时代的底层人物的故事......通过这三位作家的讲述,我发现,变化虽然很缓慢,但它是会发生的。
就像余华引用《国际歌》的那句“没有什么神仙皇帝,我们要自己救自己。
”游到海水变蓝,从某种意义上,和《国际歌》有些相似的含义。
贾平凹大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在家里的书房发现一本《贾平凹散文集》,按照我一贯的“选书”习惯,翻开正文部分第一页,看看这个作者的难度几何。
读著,发现文字挺朴实,讲的也是生活日常,我便半懂不懂地啃下来了。
现在,我脑子里已经没有关于那本翻得挺破旧的书的残留记忆了,只记得中专中文系毕业的妈妈看我又“看上”她藏书里的一本书,给我简单科普了一下——这是一个西安的作家,他的名字不读“ao”,要读“wa”(我当时脑子里出现一池塘的青蛙),是陕西方言的发音;我们读书的时候(90年代初),他特别火,大家都喜欢读。
今天看贾导的片子,才对这位生于五十年代、写作过程经常用到陕西方言的作家有了更多了解。
贾平凹二十出头的时候,也经历了一段迷茫期,他说“那时年轻,什么都想写,毕业后也是什么都写一点,到1982,83年的时候,感觉这样不行,得找个方向。
”那段时间,他决定回老家商洛待一阵。
回去后,他和两个朋友一起,每天骑着单车,在村里到处逛,感觉很痛快、自由。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在小村小诊所感冒打针,因为注射用品不干净,感染了乙肝,用了15年才治好)和最大的快乐都在这个时候。
”回忆自己和故乡重新产生联系的那段时间,贾平凹说。
那时,他开始找到自己坐标系的原点和方向,以贾家庄的人为原型,创作新的小说,从短篇到长篇。
到八十年代中期85、86年的时候,他的坐标系慢慢成型了——“站在家乡,看中国,看世界。
”贾导说,现在,他有一半的时间生活在老家汾阳(没事的时候就住这儿,有事的时候离开。
他在《十三邀》里如是回答许知远)。
他有很多电影取景在老家,现在,很多时候也去各地取景拍片(譬如这部,去了三位作家的家乡)。
无论在哪里拍摄,“汾阳是我的起点,一直给我灵感。
它是故乡,也是中国。
”汾阳就是中国,因为汾阳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县城,而中国正是由无数这样的小县城组成,而不仅是那几座大城市。
梁鸿2007年,梁鸿在北京生活第七年,读完博士,结婚生子,儿子两岁了,生活里的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走,她好像即将开启生命的新阶段。
她却感觉这样的状态不对劲。
内心有个隐约的声音,叫她回家看看。
当然,不仅仅是“看看”,她决定回老家住一段时间,写东西。
这次回去,她慢慢生出新的观察角度,重新去看待家乡的老人,家乡的河流。
她去拜访村里的老人们,发现他们经常接到在外打工者的电话,有时收到在外打工的子女寄来的汇款单,他们开心得好像过节一样。
梁鸿意识到,梁庄有很多人在外打工,虽然他们人在外地,但一直心系梁庄。
而她自己,也是这些在外工作的梁庄人的一员。
“梁庄三部曲”就此拉开帷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
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
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我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我的故乡是穰县梁庄,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
即使在我离开故乡的这十几年中,我也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它。
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
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
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
它包皮含着多少历史的矛盾与错误?
包皮含着多少生命的痛苦与呼喊?
或许,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我回到了偏远、贫穷的梁庄,踏踏实实地住了将近五个月。
每天,我和村庄里的人一起吃饭聊天,对村里的姓氏、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作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我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以及那些已经逝去的亲人。
当真正走进乡村,尤其是当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时,你会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
它存在的复杂性,它所面临的问题,它在情感上所遭遇的打击,所蕴含的新的希望,你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
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笼统的群体,你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
他们的情感、语言、智慧是如此丰富,如此深刻,即使像我这样一个以文字、思想为生的人也会对此感到震惊不已,因为这些情感、语言、智慧来自于大地及大地的生活。
”看完梁鸿的讲述,忽然想起我从2013年上大学以来在家住得最长的一段时间,每天去长江边跑步,翻翻过去的日记和同学录,读那些买了很久都没机会翻开的书,写长长的回家日记。
那时,我意识到,虽然我那旺盛的“怀远病”(Fernweh)总催我离开,但我的身体的确是最习惯这个湖南北部小镇的,这儿湿润但不带咸味的空气,长江大堤上从水面吹来的暖风,自家小菜园里爷爷种的很辣的辣椒......影片最后一名受访者是一名00后,梁鸿14岁的儿子,导演请他自我介绍。
他用标准的普通话介绍了一遍自己。
“我在河南出生,在北京长大;在人大附中念书,我的爱好是物理...”介绍完,导演抛来新的问题:“用河南话把你刚才的自我介绍再说一遍吧!
”在北京长大的大男孩听了,连连摇头:“河南话我都忘了。
”导演说,没事,试一下。
他开始小声练习,把刚才的话“翻译”成河南话版本的。
梁鸿走过来,靠着儿子坐着,说,没关系,妈妈来教你。
跟着妈妈标准的河南话,大男孩一句一句地重复了一遍。
教完后,梁鸿说:“你再来说一遍吧。
”大男孩不再拒绝,用河南话做了个完整的自我介绍,能感觉到他部分字音有些拿不准。
但是对于他来说,是否标准不重要,说河南话的过程,也是他在和自己家乡建立联结的过程。
等他长得更大一些,会更理解妈妈书里写到的那条改道的河,和村里人形容这条河的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梁鸿说,很早就生病卧床的母亲几乎不说话,在她心里,母亲就像一道沉默的阴影,直到现在,她都无法和人谈论母亲确定了自己的坐标原点后,无论看什么,好像都在“佐证”自己内在的声音。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也恰好呼应了我当下的状态。
前几天和高中闺蜜聊天,她正准备出国的GRE考试,她说,她对当下国内的现状很失望。
我说,我毕业后准备回国,继续做新闻。
她听了有些惊讶。
聊了几小时,她领会了我的决定,说:“的确,如果你人在国外,心里还是一直惦记着国内的一切,可能还是回来更好吧。
”贾平凹在《带灯》这本散文集里写过“故乡”的一种定义:夜里,看完了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带灯也在她的房间里读元天亮的书,书上说:你生那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乡也叫血地。
“故乡也叫血地”,所以,无论身在哪里,血液里仍有故乡埋下的种子。
而当这种子发芽,当这召唤再次响起的时候,你只能停下远行的脚步,重新去拥抱你的缘起。
就像我亲切的“同乡”作家沈从文说过的,“我实在是个乡下人。
”添加微信号paokaishubenxbb加入全国影迷群
4 ) 血地或应许之地
主题上,贾樟柯通过四位作家作家忆述故乡与自己文学的关系来回望历史。
电影本身试图建构起四五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历史与文学,故土与文学的关系。
贾樟柯提出的命题,是我们如何记录历史对文学书写者的经验的塑造,以及多种时空里文学、人生和乡村所呈现出的驳杂的面貌。
作家们的文字在主题、风格上都有差异,因此片子选择历时性的结构和乡土主体作为可以串联起来的主要线索,而那些对人物群像的图景式的展现和口述文学的刻意表演则流露着悲天悯人的情绪,这是导演力有不逮的一贯尝试。
或许并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导演本人当下的选择和局限,他的才不再此处,但是志却要固守此地。
文学,历史与故乡的关系如此复杂,作家的态度也截然不同,贾平凹隐忍和保守,梁鸿则是切肤的疼痛。
唯有余华,余华不是这样,他既能出乎其外,又能入乎其中。
他成长的故事,尤其是买着站铺一路向北的故事,和他说话的节奏,都证明了文学与他物有着超越性的关系。
时间,塑造了他们的文字,文字则以桥梁般承载。
贾樟柯试图建立起他的桥梁,可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结构的漫不经意与气韵的割裂,使得我不能完整地进入整部片子。
但他又有一点是可贵的,他是愿意抱着希望的,抱着这世界上尚有“蔚蓝之地”的念头或文学尚有点用处的。
因此我理解那些对着镜头慢慢念着文字的“做作”,也能感受到一种情感上的力量,即便我对此感到尴尬。
在他们念出那些文字时候,他们的动作,脸上的细节和神情,他们的语速,他们切身的经验与文字产生着共鸣。
村民们或那些乡村的表演者们,由于他们自身的阶层,在朗诵中获得了一种身份与可能性:对精神生活有着追求的同时扎根在土壤的生活。
他们是理想情况下,我们应该养育出来的人。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里形容那些摄影作品是“美学化的政治”,道理似乎差不多。
回到题目,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一种怀着对未来的期许而不断向前挥动双臂的行动,就像余华所诉说的那个在傍晚下水,晚上赤脚沿着岸边的归家的寂寞少年一样,一样地对未来茫然。
贾导似乎也很在自己的血地和“应许之地”之间感到困惑和无力,他要往前游吗?
贾樟柯只是给自己与他的观众做了一个略潦草的承诺,有这样一个应许之地,有这样一个可能:他们经由文学而获得流奶与蜜,与真正的安宁和平静。
5 ) 文学×电影:当故乡碰撞“舒适区”
文 | 乐一狸关于文学和电影,最近听到个饶有兴味的观点:剧情片可以类比为小说,艺术电影可以类比为散文,或者诗集,纪录片则可以类比为非虚构写作。
这个观点出自贾樟柯。
从业20年,始终坚持“作者电影”创作的他,今年上映了新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看贾樟柯的电影,我从不提前看评论剧透,带着一份拆礼物的心情走进影院,像拆阅一本文学作品那样,对作者电影保有惜墨如金的敬重。
电影开篇是面孔特写,许许多多普通中国人的面孔,一张张投射在大荧幕上,每个人沉默不语,却接连成一个时代的表情。
镜头推到一位平凡老者的身上,开始讲述贾樟柯的故乡——山西贾家庄的历史,随后引出建国后第一代作家:马烽。
撰写《吕梁英雄传》成名的马烽,在人生最得意时,陡然决意从北京回山西农村定居,只为完成新中国农村生活的创作任务。
理想主义的种子,从此在世代贫瘠的盐碱地上撒下绿种,贾家庄诞生了更多作家,整个村庄也从沉沉暮气的贫困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从此,这里的人们将文学视为丰收,不断举办文学庆祝活动,这也吸引了回乡休养的贾樟柯的注意,萌生拍摄文学纪录片“一个村庄的文学”的想法。
乡村与城市,伴随着现代化隆隆的脚步,不断拉满世界范围内以青年为代表的人口流动潮。
城市,成为大多数乡村少年的寻梦飞地。
片中聚焦了“50后”贾平凹、“60后”余华和“70后”梁鸿三位作家,他们主动或被动选择成为时代的观察者,凭借极高悟性和细腻笔触,留下了文学的篇章,赢得了个人声名,也从此久居大都市。
和成千上万的漂泊者一样,三位作家最初离开故土的原因,无不出自困境中的求生欲。
贾平凹受父辈“家庭成分”的影响,应征各类工作屡屡受阻,凭借儿时读《红楼梦》的眼热和一笔好字,靠写标语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从此留在西安从事文艺创作。
贾平凹在城乡生活经验的巨大差距中,隐隐感到创作的停滞,于是他归循故土,一边游历西北乡野,一边站在人生的起点遥望世界和中国,于中西交融百花齐放的文化热潮中,依凭农村生活带给他的欢乐和痛苦,寻准《浮躁》《废都》的风格和创作思路。
故乡和文学,帮贾平凹拨开了人生的迷雾。
余华的写作,始于浙江海盐的童年。
文化贫瘠的10年,首尾不全的小说残本,赋予他对故事的无限想象力。
在太平间睡午觉和百里沙浪中潜游的经验,为他提供了独特的看世界的切口。
爱情和事业的空白,迫使牙医余华远眺诊所窗外的浪漫,为了进入心心念念的文化馆,他开始写小说,无数次创作和退稿后,终于在23岁这年接到北京的电话邀约,直通文学的大门。
青年成名的功利心,遇见文学富有的大时代,催生出“业余写作”的胜利。
故乡和文学,给了余华成功的狂喜。
1973年出生在河南邓州农村的梁鸿,2000年到人民大学读博,后定居北京工作。
长期的乡土文学研究,心中始终有个声音劝她回到故乡,写点东西。
走访故土,唤起梁鸿心中从未忘却的成长之痛,这痛关于家贫,关于母亲的重疾,关于长姐的忍辱牺牲,关于父亲的气度与远见,关于村庄的绯闻和物欲。
重走梁庄和寻访全国各地梁庄人的见闻,弥合了梁鸿与父亲多年的心痕。
她终于在著写《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回溯中,辨认出苦难中一尘不染的高贵。
故乡和文学,照亮了梁鸿晦暗的少年时代。
田野摇叠的麦子,见证世世代代割麦人的沉默生长,村庄是严肃文学的土壤,向城市输送每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
余华走红后期的90年代,时代风向从文艺盛况转为全民经商,许多同路人放弃写作,眼中的光点开始追逐股市和热钱。
城市里的文艺青年,逐渐被生活消磨成不离烟酒和牌桌的中年人,千篇一律的圆润。
大多数人,就这样度过舒适且乏味的一生。
写作的孤独和城市的温水炖煮,再度刺激他思考人的一生,于是诞生了名篇《活着》。
功成名就的余华,无数次想起小时候,顺着浪潮游到遥远未知的岸边,一次次突破近海黄沙,直到闯入纯净的蔚蓝海域。
每一次搏浪前行,都淬炼着少年心性,让他勇于摆脱行医的家传,承受千百次被退稿的打击,一路流徙至命运拐点。
在北京长大上学的梁鸿之子,随母亲返乡祭祖,听长辈们讲述饥荒、瘟疫、河流改道,宛若观摩一场化外之地的魔剧。
热爱物理和电子游戏的少年,对父辈往事长久地失语,正如籍贯一栏写着“河南”的他,再不会开口说河南话。
一代人离去,一代人归来,只有村庄的河流在静静流淌。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贾樟柯近几年评分最低的影片,很难让人产生具体的观感,在我而言,就是为每个时代都必然存在的不安分与故乡之间的羁绊,平添了一份私人记述。
城市会点燃一个人的沸点,最终诞生传奇;而故乡决定了一个人的起点和归宿,滋养了文学的灵性。
6 ) 所以海水变蓝以后该往哪里游
余华说,小时候读到海水是蓝色的,可他看到的海,是黄色的。
所以要游泳,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片子是拍给海另一边的人看的,或者依然在奋力游泳的人。
贾导对自己的作者身份意识清醒,贯彻始终。
影片的基本构架,是一群出身乡土的文艺工作者的自我叙述。
大部分访谈场景都将观众与被采对象做了一定程度的视觉隔离,拒绝刻意煽情或强制带入。
镜头也并未对他们的故乡做具体客观的描述。
这里的“故乡”几乎是匿名的,是金色的麦田,蜿蜒的小路,和充满破烂招牌的街巷,是三代之内你我任何一个人的“故乡”。
是一个抽象的场域,是我们跋涉之徒的血脉之源。
有趣的是,贯穿这些分散讲述的,是刻意诗化的场景、夸张的文学朗诵、贾家庄戏台的古典配乐等。
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观者注意我们与“他们”的距离,并不断思考我们自身的位置。
有一段印象深刻的蒙太奇,是莫言、余华、西川等当代文学大拿,在某个汾阳贾家庄做文学演讲。
作者的脸、勃拉姆斯、舒曼、上帝、城市、棚拍、闪光灯、戏曲、老师、蹲着、打工……在画面与声音中迅速切换,如同飞速发展的都市景观,带着一种毫无逻辑的天经地义。
影片后半程,在梁鸿的讲述中,乡土现实与文学梦想的暧昧关系被推到前景,或者用电影本身的语境,被推到“岸边”。
梁鸿从泥土中抽身,朝着蓝色游出很远很远,却从心底感到一种“背叛”。
她选择回乡去,带着北京长大的儿子,带着自己的学生,带着对父亲的疑惑,带着对姐姐和母亲的歉疚,回乡去。
而观者,也在母子二人同框的时刻,完成了从“我们”到“他们”的链接。
PS. 小时候,郑州的天空是蓝色的。
埋头做题十二载,耳机里都是英语,再抬头的时候, 天已经灰了,而我还没有看过海。
一晃眼,大洋彼岸蓝天白云。
又十年,听见《黄河瑶》就哭,不听海浪声睡不着觉。
似乎那海,依然在别处。
那条河,也不大回得去了。
7 ) 人的根似乎不能扎在城市里
听着山西话和陕西话都很亲切。
全片都是作家与故乡的关系,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文学与家庭回忆的羁绊。
你生在那里,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乡也称为血地。
— 贾平凹看到梁鸿的故事多次落泪,姐姐读信那里让我开始怀疑是否以前的人都那么会写?
为什么一封家书如此文笔?
看完贾平凹、余华、梁鸿三位的生平故事,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当然一方面佩服他们挺过艰辛困苦的勇气,但另一方面反观自己,觉得自己没有根。
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感到失去灵魂的时候,都有一个在农村的大后方或者根据地去回归,去专心致志地享受生活和体悟人生,而我没有这个选择,我没有“老家”可以回。
人的根似乎是不能扎在城市里的。
因为柏油马路和水泥行道太硬,再顽强的树也无法在这里真正安家。
最后余华在日落后的海面上行走,说小时候看到的海都是黄的,但课本又说海是蓝的,所以自己就想一直游,游到海水变蓝。
他真的游到了。
8 ) 一部纪录片
通过多个人物自述家族和自己的过往经历,拼凑出来了在特定年代以及特定年代环境下的人物遭遇。
贾家庄、海河、山西。
这些遥远的地名因为有了人物的行为勾勒,有了一个生动的形象。
《吕梁英雄传》和吕梁文化节又是出场人物共通的引线。
英雄不无问出处,但英雄亦有来路。
听他们讲曾经的故事,听得入神。
脑中保存的历史印象和地理人文版图又扩大了一点。
片尾梁鸿的儿子想知道姥爷那辈人想不想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想不想知道外面的人是怎样生活的。
最后余华一边散步一边说出的话,已经很好的回答了这个孩子的疑问:“那个时候这里的海都是黄的,就想一直游一直游,看看能不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
9 ) 一直走到土地裂开
许知远说贾樟柯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在没有新闻的年代,不知这样的描述是否过誉,可是,平心而论,当我坐在电影院观看他的新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时,仍能感受到他十足的真诚,真诚之下,是依然试图记录时代变迁之景象的贾樟柯,一如当年在重庆长江边上拍下《三峡好人》的他。
老实讲,这是部中规中矩的纪录片,其中许多镜头甚至让我觉得过于刻意,比如让许多人朗诵那些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因为当你想要用镜头去表达一位作家、一位诗人,最简单也最失败的做法就是大量的念他的作品,正如一部电影,如果尽是旁边,那么故事本身的流畅性将大打折扣,而为了文学而文学的做法本身即是反文学的。
但这本身不重要,至少在这个时代不重要,当人们过分缺乏严肃的作品时,炫技本身也是一种不真诚,那么当我们原谅这部作品的这种刻意,我们就会看到马烽、贾平凹、梁鸿和余华等人是如何逃离农村,逃离土地去往中心,而在中心遭遇危机后,又是如何重新发现乡下,然后在中年后感伤于土地的失落。
他们的经历只能当作故事讲,并无多大的参考意义,在祖国的大地上,那些尚未离开土地人们,其实是失语的,千百年来,沉默才是他们的发言,对于这些无法逃离的人,他们的命运早已被宣判在脚下的土地上,即使离开,羁绊永远存在,而最重要的是,生活在泥土中的人们,往往对泥土没有发言权。
于是,已经离开的人感到了乡土的失落,而在其中的人,连感受失落的权利都没有,在很多时候,不仅快乐是一种特权,连伤感也是一种特权。
从而,我们需要贾樟柯,需要贾樟柯式的人物记录下那些为着生存而弯腰驼背的背影,那些在时代洪流中留在岸边的眼神。
据说贾樟柯的电影,汾阳人民都看得懂,于我而言,他的电影也几乎不存在观看门槛,而从他电影中的小人物身上,我们总能看到这个时代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而这种东西,若不通过他的电影,或许我们自身都无法发觉,正如身戴锁链而欢呼着自由。
以前我逮着学艺术的人就问,艺术是什么,但所有人给出的答案都不一致,而如果这是一个有答案的问题,那么我现在逐渐觉得人类的交流就是艺术,而能使人们放弃一切戒备,以最真诚的语言交流就是最好的艺术。
因此,好的艺术应该是不需要门槛的,就如欣赏音乐和美术并不需要你去艺术院校深造几年,尽管彻底的通俗,彻底的平等带来的也许新的反智主义,但这绝对不是使艺术束之高阁、孤芳自赏的辩护词。
可惜,生活中往往尽是阻碍交流之特权,出身、金钱、学识、职业、以及权力等等带来了独属自身的训话逻辑,而反对这些话术,重新使人们记起平等的交流,反思一如往常的生活之合理性,才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艺术面临之最重要的问题。
而这才是贾樟柯最难能可贵之处。
当你发现,这个山西导演,从青年到中年,从汾阳到蜚声国际,一直从未脱离那些仍然脚沾泥土的人,仍然为那些人的命运所牵动,仍然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记录者,这何以不让人感动?
10 ) 地域、文学、私人回忆
关于这部电影的最大感受是【遗憾】。
一来遗憾于,文学的时代已经全然过去了。
让作家来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写作经验,受众面窄到几乎可怜,即便是余华这种畅销型选手,一本《活着》就够吃一辈子的,观看他们的叙述和镜头前的表达所达到的数据量永远比不上一些游戏主播、直播带货、脱口秀表演以及热门的vlog博主。
文学被各种智能设备以及娱乐方式排挤到非常边缘的位置,尽管唏嘘,但这也难以避免,而华语文学也呈现出了堕落、矫揉造作以及圈子化,让人觉得难以接近,可有可无。
比如电影有一个细节,贾平凹的女儿说自己要发第二本诗集作品了(据说她的诗写的也实在不行),贾特别提醒她要将生活和文学分开,在生活中首先要做好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后面半句当然是非常男权和父权的发言,但将生活和文学分开恐怕的确是经验之谈,毕竟,大多数人即便不接触任何形式的文学,也能够很好地生活下去。
二来遗憾于,我国没有真正的艺术院线。
这样的纪实类型电影要和大多商业电影一起塞到电影院里,去竞争排片和票房,结果也可想而知,不过好在本片所耗费的资金成片可控。
电影最大的亮点应该是余华了,他是一个很好的叙述者,健谈、聪明、幽默,相比之下,贾平凹和梁鸿的叙述显得遥远以及略有阴沉。
鉴于电影题材的冷僻,余华的幽默恰恰也是电影所需要的的,如果不是余华,电影或许会陷入到毫无波澜的尴尬境地。
另外,和贾平凹、梁鸿也不同的是,余华是一个非常想“走出去” 的人,而贾和梁都选择了回到故乡,他们在方向和道路上也呈现出了外向和内敛,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都是成熟的且成名已久的写作者。
说一些观感方面的看法吧。
电影里有大量的面对面采访与讲述,这样的拍摄太过平实,并非是什么高明的手段,在记忆与讲述的影像化方面也许可以更丰富一些;电影有两段多次使用的配乐,一段阴沉,一段轻快明亮一些,阴沉的那一段配乐将整个电影的氛围又往冷调拉了一些,让一些片段更像是犯罪题材类型电影,或许换一段更好。
结尾极佳!
简短、干练、充满诗意,值得一个华语电影年度最佳镜头了,这种诗意要远比找人在镜头前诵读诗句来得深刻直接。
那个镜头,那个瞬间,让我觉得讲述者和掌镜者的灵魂似乎相通了,这在拍摄中是非常难得的时刻。
接着,电影也在那个高光时刻结尾,给了观看者遐想的余地和空间,这样的处理太妙了。
知乎上有人提问,《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适合怎样的人群观看?
这个问题其实挺奇怪,我觉得小学五年级文化程度及以上的所有人都能看,即便不接触所谓的文学,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得到一位作家的人生经历故事,而得益于现代的拍摄与传播媒介,这只需要耗费一张电影票的钱。
或者,文学也完全可以换一个概念,比如“故事”,写作者也无非都是讲故事的人,而据我所知,人除了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外,天然有着对故事的需求。
在过去,文学创作的确可以帮助一些人摆脱窘困的人生或者物质状况,贾平凹和余华便是很好的例子,但在现在,文学创作的好处没有那么明显了,这是一个投入与产出极不相符的项目,比如胡波,拿了奖出了书拍了电影,最后在遗书里的留言是“蚂蚁花呗快还不起了”。
当然,不同的人情况又各有不同了,也不好一概而论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时代的变化。
文学可以视作为生活的提纯与自我的游戏,想阅读的时候就去阅读,想创作的时候就去创作,想去分享也完全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写点什么,但要在日常的生活里大量地掺杂所谓的文学或者将文学当成是全部的寄托和希望,可能得到也只有失望、谎言、嘲笑以及无边的挫败感。
最后,关于本片,其他不说了,能过审也挺不容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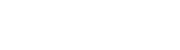







































贾平凹真苦,余华真逗,梁鸿好真,科长的众生相拍得真好
贾平凹和余华这两段都说烂了,我起码看了十几二十年了。梁鸿这个看着挺亲切,是我老家的样子。但总体而言,这算啥电影啊。
一直没打分。我就记得在平遥小城之春全程严肃看完,置否在旁边哭成了泪人,我拍拍她,说了声,不至于,不至于。余华撑起了整部电影。
还是那句话,当正在经历历史的时候,一切奇情都不及现实来的有力,三位作家的平静陈述,最能道尽那些不能忘却的铭记。余华太有才气了,是那种未经雕琢的纯粹真诚,这诗意十足的片名,竟也只是随口一说。其实片子本身说不上好,但电影的现实性和时间性在于,在何种背景下于何种境况下看到它,这部的华彩或许就是来自贾樟柯开场前和结束后说的那些话。“电影应该存在,应该与人民同在。” “没有神仙皇帝,一切都要靠自己。虽然改变很慢,但总会有,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Berlin HdBF
多数内容是杀鸡用牛刀,余华部分的好,是余华自己表达能力的好。一切都没毛病,但又好像一切都掉在地上,价值不高。
我喜欢那些尴尬的诗朗诵,因为这正是文学落入现实的真实反应,矫情,做作,还有些生硬,但是却带给普通人美好的幻想。海水不会变蓝,就像生活永远不是诗,可文学却永远存在。
余华这个人太有趣了,如蜻蜓点水随行自在。科长这部和《海上传奇》整体节奏基本一致啊。
贾樟柯是大陆一位真正能够坚持自我的导演,看看其他六代导演,就像余华说的,邓小平南巡之后,全民经商,曾经志同道合的人也都改变了志向,做起了生意。影片的最后,贾导还狠狠的隐喻了一把自己 “哪怕眼前的海是黄的,只要你一直游,一定能游到海水变蓝”
贾家村不该乱入,余华部分最生动,贾平凹有点端着。几位作家的排序来看,年代感还是比较强。
怎么讲,强忍着生理不适看了半个多钟头可以说是我的极限了。基本上这个电影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做对了的,每一帧镜头里都是傲慢,有本事你也拍苏童莫言挖耳朵?看抖音傻笑?离开了村庄就忘记村庄的人太可耻了。看到贾平凹那里实在压不住了,毁灭吧妈的
没太理清这个纪录片的线索脉络。但是余华真的挺有意思,笑的合不拢嘴的时候,突然想到他都写过什么,真是笑容僵在脸上…
真好看,充满文学感,就像散文诗,每个段落,那些放大的脸,哽咽的话,都走进了我的心。一直在想主题是什么,看到最后也没找到,但也不影响每个段落带给人的感动。余华一个人就撑的起整部纪录片……另外,我果然是不喜欢贾平凹的。
名字似乎比内容好
除了作家的叙述之外并无看点。现实生活的乡村里,还是充满很多随意的谈论和恶意的评价(梁鸿父亲的遭遇),轻而易举地伤人,然后使人钝化。文学是一种躲藏。
像五月碧云天镜头前,学词的老人,说着,走了,走了(全片的朗读是一种讽刺吗?那科长可太高明了,给余华加一星)
影像的精致,掩盖不住内容苍白无力,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新旧农村的交替,谈不上有什么深度的挖掘,就像在路上偶遇旧友闲聊几句然后便匆匆离去。形式感很强,打光也讲究,干净明亮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田间地头的诗朗诵,应该放到央视农业频道当成公益广告轮播一年。原来不只是罐头会过期,纸条也会过期,把所有的赞美都给老实人余华老师!余华游到海水变蓝,科长拍到一半收工!
余华也太有趣了吧
片名成功一半。纪录片看什么蓝色的海,纪录片就要看黄色的海啊。投身下去的水明明不是蓝色的,非要“游”到梦想实现,那只能用障眼法,别人告诉你,游得太卖力太辛苦,海水已经变蓝啦。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亚洲首映。关于我们是从哪里走来的、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宏大又细密,平静而深情。片名是一个太棒的意象,凝结了很长的路,很复杂的心境。从混沌处出发,游到深远处,得到的是前行的满足,还是失去出发点和方向感的迷茫惆怅,各人自知。影片的影像、声音、音乐都太棒了,这是真正的电影,看大银幕是一种享受。
电影中最喜欢的一幕是很多人印象中的绿皮火车,似乎永远和肮脏、拥挤、嘈杂、贫穷、难以忍受的充斥于车厢的每个角落的泡面味道相关,但当熟悉的Time to say goodbye的旋律在电影中响起时,贾樟柯的镜头对准了车厢里那一张张平凡的面孔,一双双陌生又熟悉的眼睛,音乐和影像结合,随着镜头的来回切换推移,灵魂在黑暗中得到某种升华,我在影院的黑暗里感叹影像艺术的奇妙无比!这种感觉不亚于我读聂鲁达的诗的畅快,不亚于我站在《水中的奥菲莉娅》的触动,不亚于我叹赏博尔赫斯往水里扔硬币这一情节的惊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