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症》剧情介绍
浪漫之夜,才华横溢的美丽少女贾斯汀(克斯汀·邓斯特 Kirsten Dunst 饰)和心爱的麦克(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 Alexander Skarsgård 饰)步入婚礼殿堂,姐姐克莱尔(夏洛特·甘斯布 Charlotte Gainsbourg 饰)和家人们为了她一掷千金,尽心操持。然而莫名的恐慌与悲伤袭上心头,令贾斯汀整晚郁郁寡欢,她的婚姻刚刚开始就已到了破败的边缘,与亲友同事的关系也变得分外紧张。克莱尔试图将妹妹带出忧郁症的困扰,然而收效甚微。与此同时,一颗神秘的小行星正向地球飞速逼近,似乎正是它带来了贾斯汀的忧郁,又似乎那原本郁结心中的烦恼只不过被它释放了而已…… 本片荣获2011年第64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新常态蜡笔小新:呼风唤雨!黄金的间谍大作战洪熙官之天地英雄烈焰新娘好雨知时节幸存的女孩峡谷西班牙女佣妈妈!不要抛弃我远山的红叶高潮天地创造设计部火光之色唐砖下之灵域双生浮动母女情深扪心问诊第三季爱丽丝小姐家的地炉旁边小喽啰隔窗恋爱阴阳打更人极品老妈第四季决战狂沙镇命之途阿米娜阴守忍者无言黑暗曼波舞王37她的气味
《忧郁症》长篇影评
1 ) 闪灵大战"吸血鬼"
《睡梦医生》个人观影随笔,非正经影评 非常精彩的电影,为什么分这么低呢?
豆瓣评分也人格分裂了吧,才6.9分,前面看的另一部《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竟然8.1分,看过《闪灵》应该能理解很多梗,我觉得衔接的很棒,故事完整性也不错,虽然拍的有点像原力,但是毕竟《闪灵》已经表现过了,相当于是一个引子,我想部分人不喜欢的原因,可能是觉得库布里克拍的太神了,《睡梦医生》揭开了他的神秘面纱,世俗化,工具化,像x战警,像超级英雄,又像星球大战,更像吸血鬼,就是不像闪灵,好在我看得津津有味,三条线并驾齐驱,彼此交错,算不上神作,也绝对精彩,影片很多地方有卖弄情怀的嫌疑,尤其是最后,一些《闪灵》里的桥段,直接搬过来,对于推动剧情也没什么作用,可能导演只是想告诉大家这是续集,或是给那些没有看过闪灵的人感受一下经典桥段的魅力. 有几点我想吐槽,第一,反派女主实在是太漂亮了,根本让人恨不起来,不管他是狂笑,愤怒,傲慢,还是暴走,在我眼里他都是小捶捶捶你胸口,第二,黑人小女孩儿,查克拉爆满的闪灵能力也就算了,惊人的执行力和反常的成熟表现才更恐怖,甚至一度让我怀疑她才是终极大boss,第三,电影虽然有三条线,但是主角就只有三个人,其他人都是酱油角色,伊万和那位同事,光两个人就干掉了80%的反派,最后还搬出了杀手锏,太不公平了,我都觉得反派好可怜
2 ) 舊日的優雅
闪灵讲了一个老派的故事,悠悠哉哉的黄金时代的酒店,悠悠哉哉的威士忌,只有主角们在发疯,鬼们,其实悠闲的很。
forever and ever and ever那一对小漂亮更是坦然的让人心脏停止。
女主角的惊吓苦情脸也是绝妙。
看了一点点电影,其实能记得内容到细节甚至看了两遍的电影,真的不多。
当时只是觉得,好看而已。
再看到这部。
是几万米高空的完全空闲时间,无法直视。
首先,导演企图解释,男人和小孩各种灵异,一堆怪人各种灵异,这种事情,何必要解释。
其次,套旧梗,生怕观众看不明白的各种回溯,就好比西瓜和红宝石,这个怎么对比。
随便从颜色到音乐到节奏到演员到台词,回溯一下就给这个新片一个减号。
最后,立意,其实灵异怪人和美女坏蛋还是ok看的,这一组完全值得展开,结果砰砰砰的就都挂了。
巫不巫鬼不鬼怪不怪的。
还非要烧了那个印第安人保护区的房子。
那种大佬拿着雪茄,抱着美女只当是摆设的气质完全没有了。
酒店吧台的酒保一段也是非常惊艳的一个点,新的片导演应该也喜欢,可惜用的惨不忍睹。
烂片。
颇有预言感的赤裸着的当下的烂片。
这要不是触及了闪灵,一个字都是多余写。
3 ) 小鬼招魂
重要剧透:片中最重要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最后一起去了酒店。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星系……年幼的主角丹尼跟随父母来到位于科罗拉多的远望酒店暂住。
以写作为生的父亲杰克在灵感枯竭的焦虑感折磨之下,精神崩溃,遭到酒店邪灵的吞噬。
丹尼和母亲在酒店厨师Hallorann的帮助下,拼死逃出了父亲的魔掌。
丹尼其实是一个原力敏感者,他的绝地武士名字是欧比旺肯诺比。
在他这个维度,原力被称作闪灵。
Hallorann就像其他绝地大师一样,死了以后还阴魂不散,冷不防在欧比旺面前显灵,说一些高深莫测的话。
小欧比旺离开远望酒店以后,时常被噩梦中的妖魔鬼怪吓尿。
只有让自己的原力觉醒,他才能战胜恐惧。
第一幕的催化剂是主角丹尼学会用意念世界里的盒子封印恶灵。
他获得了超能力,貌似生活应该开始变得顺利起来了。
然而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主人公,他的缺陷也是与这种超能力相伴的:他害怕显露出与众不同的一面,因此在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过分低调,甚至可以说是碌碌无为。
长大后的欧比旺完全沦为一个废柴大叔,成天喝酒、打架、约[哔]、磕[哔],经常一觉醒来先把脑袋塞到马桶里一吐为快。
有的时候运气不好,药掉进马桶里,还不得不整个人钻进苏格兰最恶心的马桶里去捡药。
影片在第一幕分成三条线索,男主角丹尼只是其中一支,另外两条线分别关于女主角Abra和反派Rose。
其实对故事起到主要推进作用的是反派这条线,这伙人登场早于两位主角,在影片开场画面即展现出残害儿童的邪恶一面。
到第一幕后半段的争执、辩论部分,三股势力已全部浮出水面。
男主角纠结的是他还要不要继续过这样堕落的生活;女主角则展现出明显不被她的父母欣赏的异能天赋;反派势力的争辩主要围绕拉新人入伙这件事展开。
Rose一伙想要拉拢的是一个专门利用催眠能力惩罚恋童癖变态大叔的“水果硬糖”。
我一度以为这个说睡就睡,指哪睡哪的少女才是片名所指的“睡梦医生”,结果她矜持了没有两下就上了反派的贼船,从专治恋童癖的女侠变成了诱拐虐杀幼童团伙的骨干成员。
大反派Rose给她开的价码是永葆青春。
伴随着她的入伙仪式,故事进入了第二幕。
欧比旺远走他乡,参加了戒酒互助会,还在医院做起了临终关怀的护工,他利用自己的原力帮助病入膏肓的老人们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跟他搭档的是一只猫。
这只猫基本上就跟柯南一样,走到哪就让人死到哪。
第二幕的游戏、娱乐部分就是主角和反派分别用他们的超能力帮助和伤害他人。
影片的B故事则是男主角丹尼与女主角Abra的友情,两人会在这一段交往中,克服自身性格缺陷。
在第二幕开始后不久,丹尼在黑板上发现了Abra的留言,这是A、B故事的第一次交汇。
此后二人就成了笔友。
故事推进至临近中点处,情路坎坷的奇迹男孩惊喜亮相。
自从因为胡乱拿老爸的无人机去偷窥别人亲嘴而被禁足之后,他就在家里刻苦锻炼臂力,终于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棒球运动员。
可惜即使他拥有了强健的体魄,还是敌不过擅长催眠术的诱拐犯。
如果他当时戴的是铁血战士的手套而不是平平无奇的棒球手套,胜算应该还会高一点。
反派一伙保持青春的方式就是吸收小孩子因恐惧而泄露出的闪灵气息。
这让我想到了近年来甚嚣尘上的关于富豪通过与年轻人换血延长寿命的都市传说。
奇迹男孩遭到虐杀的过程被“三眼乌鸦”Abra感知到了。
之所以说她是三眼乌鸦,是因为她也喜欢潜入别人的意识、发功时爱翻白眼,而且她的宿敌也是一帮子眼珠发蓝光的怪物。
不过她比起那位我们更熟悉的、在权力的游戏中躺赢的三眼乌鸦,有个最重要的优势,就是腿脚比较灵活。
光是在黑板上留言还不足以表达她的关切,她干脆亲自跑到了欧比旺面前。
影片中点处,A、B故事产生了更深的交汇。
Abra称呼欧比旺为丹尼叔叔,她希望两人联手利用超能力为死去的男孩讨回公道。
丹尼拒绝了她的邀请,并劝她低调行事。
后来他的精神导师再次显灵,鼓励他去帮助小姑娘。
这个一直游离在主线故事之外的男主角终于下定决心参与到正邪对抗中来,还把自己的好朋友也拖下水。
第二幕后半段的“恶人逼近”主要是Abra和敌人的数次交锋,每一次都是主动出击的反派惨遭吊打,给人一种在看《小鬼当家》的感觉。
这种吊打在剧情设置上应当属于“虚假的胜利”,然而过于悬殊的实力对比,让这几场胜利显得完全不虚。
反派倾巢出动来抓捕女主角结果遭到各个击破的那场树林枪战,算是把上面提到的那种《小鬼当家》质感发挥到了顶点,配乐要是再欢快一点的话,完全可以当喜剧来看。
这一段让我觉得别扭的主要原因,在于一部带有强烈奇幻元素的影片,除了决战以外最重要的一场动作戏居然是与核心设定无关的战斗方式,颇有凑数之嫌。
随着这场枪战戏结束,影片终于也摆脱了《小鬼当家》既视感。
催眠女弥留之际施展了一次超能力,带走了主角的朋友——一个非常典型的注定要在恐怖片里用自己一条命换回白人主角一条命的有色裔悲催配角。
反派团伙的二号人物也趁同伙们送死打掩护的时候潜入女主角家,杀死了她的父亲,并将她绑架。
主角一方陷入了“一切尽失”的境地。
遭遇重大挫折之后陷入“灵魂黑夜”的丹尼仓皇逃回住处,几乎要再度向酒瘾屈服。
墙壁上Abra的留言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他发动自己的闪灵,用心电感应与Abra交流,联手解决掉了女反派的最后一个同伙。
进入第三幕,两位主角成功会师,A、B故事再次交汇。
正邪双方都准备使出浑身解数来展开最后的决战,反派吸光了积攒多年的闪灵气息,功力大增;主角则准备发动一场“风暴袭击城堡”。
丹尼选择的决战地点是留给他深重童年阴影的远望酒店。
五要点结局的第一步是集结队伍、厉兵秣马,丹尼进入酒店唤醒恶灵,设置陷阱,这里他又重新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后者已经成为酒店里的一名酒保,不但名字、职业变了,连演员都变了,顺带一提,本片似乎一个老版的演员都没有沿用,相比之下,特地用特效还原三主角二十多年前面容的《终结者6》至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讲情怀的;第二步是执行计划,正邪双方在当年杰克尼克尔森码字的酒店大厅里对峙,丹尼释放出被他困在盒子里的恶灵,女反派被吞噬 看似胜利在望;第三步是高塔意外,解决女反派之后,丹尼也遭到恶灵侵袭,像他父亲当年一样,对孩子举起了斧头;第四步是再次深挖,Abra唤醒了丹尼仅存的意识,后者为她争取了逃出酒店的时间;最后尘埃落定,丹尼在大火中与这间邪恶的酒店同归于烬。
终场画面,丹尼的肉体虽然被消灭了,但魂魄仍然时常陪在Abra的身边。
两人都不再隐藏真正的自己,骄傲地展示闪灵能力。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最值得夸的一点,是给喜爱丽贝卡弗格森小姐姐的观众提供了一次在看完《黑衣人4》之后洗眼睛的机会——放弃雷人造型,小姐姐终于又美回了原来的高度,虽然角色本身乏善可陈,但是演员的个人魅力能弥补一大截。
本片从片头刚出厂标时就开始薅《闪灵》的情怀羊毛,一直薅到结尾。
然而通过上面的剧情介绍,应该都能看出来,故事的主线其实跟《闪灵》没什么关系。
这个故事完全可以让小女孩做第一主角,把她的导师改成随便哪个别人,也完全成立。
当然,影片故事的单调乏味也会因此暴露无遗。
作为核心卖点的致敬《闪灵》部分,主要集中在影片的第三幕,这也是预告片素材的主要来源。
本片表面上看似乎是男主角因为结识了小女孩进而使自身的人格得到完善,其实反过来看也同样成立,甚至会让剧情更加顺畅。
所以丹尼本应是小女孩的陪衬,他这个主角身份仅仅是来源于戏份、演员知名度以及该角色与大名鼎鼎的《闪灵》的渊源。
这种主角带着自己的创伤乱入到别人的危机事件并成功抢了主线故事风头的设定,很像前几年的《招魂2》。
那部电影的核心事件本来应该是解决英国的吵闹鬼,但是最后的决战却被替换成了从美国赶来捉鬼的女主角与她随身携带的鬼修女的斗法;本片也是如此,本来应该是小姑娘和礼帽女的异能互斗,最后却替换成了丹尼与他随身携带的酒店恶灵的恩怨了结。
观影过程中大家很容易被视觉奇观唬住,尤其本片又充满了对《闪灵》的致敬,更容易让观众情怀上头而忽略了影片在叙事方面的生拉硬扯、强行拼凑。
我最早知道这部电影是通过《小丑》之前贴的预告片。
在写《小丑》的那篇东西里我也断言过,《闪灵》也好,《小丑》也好,如果好死不死拥有了续集,那肯定跟它们本身不是一个物种。
《闪灵》是包着恐怖片外壳的惊悚片,而本片是包着恐怖片外壳的奇幻片。
之所以说二者都包着恐怖片外壳,是因为两部电影都有鬼,而且鬼的出现方式以及本身形象还是比较吓人的。
但是《闪灵》最让人震撼的不是闹鬼的视觉冲击,而是主人公心灵扭曲的过程;类似地,本片的重头戏不在鬼的身上,而在正邪双方的超能力对决。
所以本片当然跟《闪灵》不是一个片种,本片的同类是《哈利波特》和《X战警》。
其实《闪灵》也是有奇幻元素的,但是因为整体风格太过冷硬扎实,少了一点天马行空的卡通感,反而会导致我这种自作聪明的观众选择性忽略其中的奇幻元素。
这次结合续集,重新回去看《闪灵》,才反应过来,原来黑人大厨和小丹尼那段关于“闪灵”超能力的对话不是瞎扯淡,他们的心电感应也不是剧情需要的巧合。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睡梦医生》对于观众进一步了解《闪灵》还是能起到一些积极作用的。
之前我擅自猜度本片的立项目的是为了跟《小丑回魂》组建一个“斯蒂芬金电影宇宙”,如今看来似乎是我想多了,本片并没有跟《小丑回魂》形成联动,甚至《小丑回魂》自己的续集都有一种赶紧对付过去完事儿的乏力感,压根儿没有一个要组建宇宙的干劲。
作为一个喜欢诛心的人,我现在又转变了怀疑的思路,认定本片是华纳兄弟看着去年《头号玩家》那段致敬《闪灵》的戏份反响不错,所以搞了一次更大尺度的致敬。
有《头号玩家》珠玉在前,“大尺度”也就成了同样吃《闪灵》红利的本片存在的主要价值了。
《头号玩家》里主角们发现第二把钥匙指向《闪灵》,主要通过那句谜语“被创造者厌弃的造物”,这背后是一段《闪灵》原著小说作者斯蒂芬金不满库布里克电影改编的典故。
我猜相比《闪灵》,斯蒂芬金先生应该会看本片更顺眼些,因为本片对奇幻设定的依赖度更高,也就意味着导演得从原著吸收更多养分,当然会更尊重原著。
不过“尊重原著的改编”和“好的改编”经常不能同时存在于一部电影上。
比如金庸先生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家记住的要么是《东方不败》这种魔改的,要么是《东邪西毒》这种串味儿成古龙先生风格的,忠于原著的反倒没有在影坛留下什么痕迹。
还有一些原著本身作为文学读物没有多高的地位,改编成电影却成为一代经典的,比如同样由库布里克执导的《发条橙》。
当然,这些都是电影方面的例子,如果是电视剧的话,资金、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改编时还是忠于原著为好。
这不是库布里克导演的电影第一次强行被续。
之前他的《2001太空漫游》有部续集《2010威震太阳神》,也是换了别的导演,有小说家的原著打底。
那部电影当然也不烂,还在当年奥斯卡收获了一堆装修奖提名,只是相比前作显得过于平庸罢了。
如今无论是《2001》还是《2010》都过去很久了,尤其是《2001》,去年上映50周年是个炒冷饭的好时机,然而好莱坞的大佬们居然没对它下手,真让人意外。
不过现在开始也不算晚。
既然《闪灵》的续集可以拍成《X战警》,那么我觉得《2001》在新世纪的续集照着《银河护卫队》的路子拍成沙雕喜剧,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4 ) 注定无法超越经典,那就做好自己的噩梦
近年来,影视行业流行于改编各种热门经典IP;而拍摄续集往往是双刃剑,一方面能满足粉丝的情怀,另一方也可能颠覆甚至扭曲原作,引起原作粉的反感。
已经在欧美地区上映的《睡梦医生》便是电影大师库布里克经典恐怖片《闪灵》的续集。
就目前IMDB给出的7.6份、烂番茄指数77%来看,说明这部续集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
当年,大导演库布里克“凭借”《闪灵》在1981年提名了金酸梅奖(是的,你没有看错),险些就中奖了。
而随着时间地不断推移,人们后知后觉地发现这其实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不仅为其正名,而后的无数惊悚电影都曾向这部经典之作“取经”。
这部电影在上映后的长达40年里,没有导演敢去翻拍它,或许正是因为《闪灵》在人类影史中有着难以替代的高度。
而《睡梦医生》首次尝试续写《闪灵》,不得不说是十分大胆的行为,是否能满足影迷极高的期待,则有待时间去证明。
此次的续集让人联想到2017年的《银翼杀手2049》,作为《银翼杀手》暌违35年的首部续集,虽然口碑分化严重,但总体还算成功,甚至被一部分影迷奉为“神作”。
影片《睡梦医生》的导演迈克·弗拉纳根向来擅长拍摄B级恐怖片,去年由他执导的《鬼入侵》剧集口碑爆棚,在IMDB高达8.7分(13万人参与打分)。
看得出来,迈克·弗拉纳根的电影主打的并不是烂俗的血腥视觉系,而是将温情与暗黑相互交织;其对于时空的转换穿插、人物如何战胜黑暗心理等,也都玩得游刃有余。
可以说,《睡梦医生》全然汲取了导演在创作《鬼入侵》时的优点,而4500万美元的投资也使得这部电影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细节上也更趋于丰满。
值得一提的是,迈克·弗拉纳根除了担任《睡梦医生》的导演外,还包办了剪辑、摄影和编剧。
而伊万·麦格雷格(选角得到了《闪灵》原著作者史蒂芬·金的认可)和丽贝卡·弗格森两位演员的加入,则更让这部电影看点满满。
影片《睡梦医生》讲述的是《闪灵》主人公杰克的儿子丹尼和母亲在在逃出父亲魔掌后的故事。
天生便拥有“闪灵”超能力的丹尼,在成年后逐渐地摆脱了童年创伤,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这是电影的第一条故事线。
与此同时,小镇上出现了一名同样拥有“闪灵”超能力的少女阿布拉,这是第二条故事线。
而第三条故事线则从一个名为“真结族”的地下组织展开,这个组织的成员皆是拥有“闪灵”功能的人,他们为了延长自己的寿命,需要吸取“精力”,即从同样拥有“闪灵”能力的活体中吞食气魄。
当该组织利用超能力捕捉到了小女孩阿布拉的气息时,第三条线和第二条线开始交织。
也正是在这时,代表正义力量的丹尼和小女孩开始联合与真结族斗智斗勇。
电影完成了一二三条线的汇聚,这一联结最终又导向了那个最原始的母题:丹尼如何与根深蒂固的记忆伤痕作斗争?
而这一切都要回到整个故事的起点,也就是《闪灵》中悲剧的发生点——坐落在一片雪地中的全景酒店。
导演迈克·弗拉纳根指明了一条精神救赎之路:唯有丹尼真正直面自己的创伤,才有被救赎的可能。
这样的设定,给予了导演将《闪灵》中的经典场景无缝对接进《睡梦医生》的可能,那些穿梭其间的致敬桥段足以让很多影迷叹为观止。
电影《睡梦医生》的片头,便重现了《闪灵》中全景酒店经典的地毯花纹。
镜头慢慢重现了童年丹尼骑着童车穿梭在酒店门廊间的片段,斯坦尼康的稳定跟拍镜头则为整部影片奠定了心理惊悚的基调。
在《闪灵》中,这条走廊几乎涵盖了各种恐怖元素。
譬如头身比例极为失调诡异的双胞胎姐妹,令人毛骨悚然充满各种巧合的237号房间,血水漫灌的幕布,琳琅满目却空无几人的pub等等,都与这条走廊有关。
而《睡梦医生》在展现这些恐怖元素时,几乎是原汁原味地重塑了库布里克式的经典场景,这不仅是出于对经典的尊敬,无形中也为本片增添了一种时空置换的错觉和迷幻感。
本片中的童年丹尼在长廊的召唤下,打开了237的房门,如同时光穿越再次看到了当年父亲所目睹的浴室裸女,这一象征性符号贯穿了整部《睡眠医生》。
导演为丹尼设计了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拯救疗法:想象自己的大脑中有无数的盒子,通过意志力将那些黑色的记忆紧紧关在盒子里。
这一设定,是导演精心铺陈的心理细节,也对之后的楼梯大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条走廊或许可以看作丹尼的恐怖记忆长河,它深深根植于丹尼的血液中,是他童年记忆中绕不开的梦魇。
某种程度上,这样沉重的记忆负担也决定了丹尼日后的性格:忧郁深沉,有逃避自我的倾向,是个不折不扣的悲观主义者。
导演设计的对白精巧地临摹了丹尼的性格。
譬如“整个世界只是一座拥有新鲜空气的疗养院罢了”、“我们都正在死去”这样低沉阴郁的话语,都在暗示着看似摆脱记忆困境的丹尼,实则依旧在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困兽之斗;只不过是以一种更为消极的方式做着隐性抗争。
他不像那位14岁少女有着满腔的元气和斗志,在面对黑暗来袭时,他显得较为保守,最初并不情愿采用攻击的姿态去抵抗邪恶。
与《闪灵》将恐怖置入生活的手法不同,《睡梦医生》的恐怖氛围营造更为直接,而非“循序渐进”式的。
但它又不同于jump scare,它总能先给予观众喘息空间,再推动惊悚爆发点。
换句话说,《闪灵》的恐怖营造手法是较为古典式的,但后劲更足;而《睡梦医生》采用的是与《招魂》等现代恐怖片较为类似的手法,当然也展现了导演在商业上的雄心。
真结族的集体骚动,为全片的高潮到来悄悄蓄力着。
无疑,导演首创的“真结组织”是电影中的另一大看点。
这个组织兼具古典和现代,他们吞噬活人气魄的姿态颇有“吸血鬼”的味道,哥特式画风也为这一群体的存在披上了神秘诡谲的外衣。
他们生活在阴暗、偏远的城市边缘,如同导演对现代社会的嘲讽,这种讽刺是多维度的:一方面,拥有“闪灵”特性的群体不被社会接受和承认,如少女和丹尼或是真结族,他们在世人眼里,永远都是格格不入的怪胎;而另一方面,他们身上的特异功能则赋予了他们洞悉万物的能力,能够超前地感知周遭,无论是福报抑或凶险。
在此,“闪灵”的特异功能被导演赋予了毁灭和重生的意味。
它能让你瞬间坠入地狱之中,与黑暗融为一体,即真结组成员所说的“转化”(turn)洗礼,但当“黑化”之后,他们便滥杀无辜以求青春永葆;与此同时,它所承载的记忆重量也能让你变得善良,从而敏感地感知正义与黑暗。
就如少女阿布拉,她预知到棒球男孩的遭遇之后,便毫不犹豫地决定打败真结族以安息棒球男孩的灵魂。
在这两层意味的加持下,丹尼的心理轨迹变得更加立体化,而非流于表面。
电影聚焦于成年后的丹尼,他戒了酒,成了一名安养院的睡眠医生。
在与少女阿布拉有了奇妙的联结之后,他决定前往自己记忆的危险之地——全景酒店。
此时的全景酒店已经没落,从外表上看去沦为了一具毫无灵魂的破败的建筑。
但当丹尼走进酒店,一切犹如40年前那样,光明与黑暗相互纠缠着,这也暗示丹尼看似软弱的性格里挣扎着的韧度。
导演在这里数度切换全景,展现《闪灵》中极为经典的场景,也彰显了叙事上的变奏张力:主人公的救赎之路总是遍布荆棘,险象丛生。
整座酒店可以看作是属于丹尼的“记忆迷宫”。
在pub里面,他再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正是当年对父亲的复杂情感才铸造出丹尼如今的人生。
多年来,他的整个人生一直处于父亲的阴影中,难以见光。
这也是他后来和母亲搬到佛罗里达的原因。
导演设置的酒吧对话,将丹尼父亲塑造为一个不负责任、厌倦家庭生活的男人,这一点确实和前作《闪灵》没有太大的偏差,也算是一种延续。
导演并不打算仅仅通过俗套的和解式结尾终结一切,将这场对话看成丹尼情绪的宣泄或许更为合适。
它并未让丹尼找到答案,但暗示了一个极为关键的信息:丹尼并不会追随自己父亲的命运。
父子的重聚戏码在全片的诡异基调下充满了温情与暗黑杂糅的奇幻感,真的十分迈克·弗拉纳根了。
影片高潮处的斧头大战和迷宫追逐戏,无疑都是对《闪灵》的致敬。
对于丹尼而言,《睡梦医生》这部电影就像是一次精神救赎之旅。
最终,他与酒店同归于尽,奔赴了属于他自己的命运。
而少女阿布拉正如同当年的丹尼,要独自面对记忆中的黑暗面(结尾的“浴室裸女”),然后一生与之战斗。
相比《闪灵》的寓意丰富,《睡梦医生》更加通俗化,并不会有“get不到”的技术性问题。
作为一部经典电影的续集,从商业片的角度来看,《睡梦医生》完成度较高,视觉和心理冲击也都属于上乘,值得一看。
作者| Ella;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5 ) 像恐怖榜单Top1致敬
远望酒店(《闪灵》)已经建成,今后的导演只是修饰和完美,正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睡梦医生》才能够做到更多,忽略狗尾续貂的争议,脱离前作换一个角度思考,我们更应该庆幸这不是一次对伟大的库布里克拙劣模仿,而是完成了对经典的重构,将火炬传递给有机后の浪,让星星之火燃烧持续闪耀如哈洛兰之于丹尼,如丹尼之于阿布拉,如果诅咒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轮回,那么守护亦是,电影与现实构成了互文,例如丹尼在几十年成长的时间里都在竭力摆脱父亲的阴影,库布里克与《闪灵》就像是悬在酒店上方的两朵乌云,无意对库神的冒犯,勉强求全,等于故步自封;所谓大成若缺,有缺憾才会有进步,经典是一座无可逾越的高山,那就“走出去”去征服下一座山峰,它不是《闪灵2》,是《睡梦医生》把《闪灵》比作一部纯正的恐怖片,《医生》就更像是它的拓展资料片,库神无意去解释的,续作对闪灵现象进行了详实的解释说明,大量对《闪灵》元素的致敬,237房间是梦开始的地方,那就让一切从这里结束,直面自己内心的 ,这才是对闪灵和远望酒店最好的临终关怀。
6 ) 睡梦医生|闪灵
对恐怖片一直没太多的感觉,所以这部《闪灵》续集,其实也没太多的期待。
故事里头倒是致敬了大量《闪灵》的镜头,如果是《闪灵》的粉丝,大概会非常代入。
不过,即便是没看过《闪灵》,大概也不影响看这个故事,完整性还是不错的。
故事不妨用我大天朝的“语言”来翻译一下。
传说中,有这么一群“妖怪”,靠吸食“日月精华”维持生命,这些“妖怪”,针对猎物,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选择性的,那些“天赋异禀”的,是最佳对象,但是这毕竟不常有,所以“妖怪们”有时候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以“数量”来弥补质量。
在“妖怪们”自成体系的同时,其实也有一部分发现了“原力”,自我觉醒。
所以体系内的“妖怪们”,在猎食的过程中,也注意发现自己的“同伴”,拉“她”入伙,也是“妖怪们”的常规工作。
有黑就有白,这“逆天”的操作,人类是拿它没办法了,但是,自我觉醒里头总是会有那么一两个“异类”。
故事里头的小女孩,是个“天赋异禀”,自然成为了“妖怪们”猎食的最佳对象。
小女孩是“天选之女”,但在先期,还属于需要保护的对象,她的天赋,还不足以对抗已经形成体系的“妖怪们”。
这个时候,《闪灵》的主角出场。
当年的“妖怪”,早已跳出五行之外,彻底洗白。
面对“妖怪们”的肆虐,当年的大神实在看不过去了,于是和小女孩一起联手,把这个“体系”干了个天翻地覆。
故事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基本上和当年梁山好汉一开始聚首,然后被招安,然后反过头来对付方腊差不多。
7 ) 能力是诅咒
拥有异能是gift还是curse,往往因人而异。
但大抵上对坏人都是gift,对好人多是curse。
这一是出于欲扬先抑的表现手法,另一点也是因为好人往往想要泯然众人,只有坏人才想鹤立鸡群。
好人一定要表现得,我不要,我不能,我不想,好吧是你逼我的。
Rose一众各有异能,且达成永久联盟。
然而除了为了活下去而找精气外,居然只是作为流浪族群四处奔波,多少也是有些可悲。
杀人自然是大恶,但他们的恶却只限于让自己活下去,而居然没有想要攫取更大的利益。
按理说历遍世事,又能力超人,完全可以成个财阀,当个政客,建个集团,有钱有权虽说对他们来说不值一哂,但绝对更利于寻找精气。
开个房车你跨个州还得几天,坐飞机找遍全球不好么。
格局还是太小。
Abra在无人引导的前提下,就会给Rose设陷阱。
要知道同样的情况可是把童年的Dan吓出尿来的。
而且她对于自己的能力显然是兴奋的,这和Dan的压抑十分不同。
因此如不好好引导,她的结局是另一个Dan还是另一个Rose是不好说的。
不过结尾处Dan以Dick出现在他面前的方式出现在Abra面前,也算是一个传承。
电影本身质量不错,即便不拿《闪灵》做噱头,自身剧本也是过硬的。
主要人物的性格和行为动机都说得过去。
我更唏嘘的倒是Billy这个角色,介绍住处时候,房东问他你确认要为这个人做担保么,他斩钉截铁的肯定,是因为我从你眼里看到了熟悉的眼神,我知道你不是坏人。
但不是坏人不代表不会带来厄运。
凌晨四点被叫起来送死。
你知道你要对付的是异能者,为什么还要叫一个普通人同行。
Dan的这个行为是我最为不解的,还记得Abra第一次来找你,你是如何回绝的么。
你不想卷入时拒绝,当你下定决心时候就不管别人了么。
男人在做危险工作时候,会不会找老弱妇孺帮忙呢。
同理,在异能人对付异能人的战斗中,你找普通人帮忙,与此何异。
如果善良也是种能力,显然这种能力对Billy来说是个curse。
8 ) 三线汇一:闪灵者的故事
《闪灵》的名字如雷贯耳,各种片段经典流传。
众所周知,经典佳片的续作很难超越前作,我第一次看《睡眠医生》的时候期待值不高,长,拖沓,不恐怖,不想打分;第二次看,有点意思,写了还不错的短评;刚才看了第三遍,很想写点个人观点,佳片与否见仁见智,随意分享。
这个故事共有三条叙事线,每条叙事线的故事都是围绕闪灵者的故事展开,三条线通过追查谋害闪灵男孩凶手的主线汇入一条。
叙事线A:帽子罗西她戴着黑帽子,感应其他闪灵者,并通过杀死年幼闪灵者、吸食他们的气实现青春永驻、长生不老,在漫长的作恶过程中吸引了一帮为虎作伥的闪灵者。
这条线中,她一遍寻找、谋害孩子,一边寻找帮凶,有个15岁的闪灵女孩,能用意念控制别人的思维,她受恋童癖之害,利用闪灵报复恋童癖,被罗西拉入作恶阵营(故事设定:闪灵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能让人长生不老的气也会不断减少,15岁对罗西而言太老了),在意念女孩的控制下,这帮恶徒残忍杀害了棒球男孩闪灵者…叙事线B:盒子丹(《闪灵》主角儿子)他从小能看到鬼魂(恶灵),做梦经常梦见,生活中也经常看到,苦不堪言,幸好他有个好妈妈。
在丹小的时候,有个鬼魂黑人大叔(个人理解是丹的善面)送给丹一个盒子,丹在他的思维迷宫中将他看到的鬼魂一一装进盒子,这个方法让他不再恐惧,维系生活。
丹长大后,此时母亲去世、终日酗酒、生活潦倒,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漫无目的来到一座小镇,遇见很多好人,帮助他戒酒,并在临终关怀老人院找到一份工作(此处对比极佳,他利用自己的天赋帮助老人走得不那么痛苦,有人却在用天赋害人)。
叙事线C:图书馆阿布拉她家庭幸福、天赋异禀,很小的时候就能发现并掌控自己的闪灵天赋,她在自己的思维迷宫中建立了一座图书馆,有记忆、有陷阱。
同时,她和帽子罗西一样,拥有感应其他闪灵者的天赋,这个天赋使她对于棒球男孩的死亡感同身受,并逐渐发现帽子罗西一伙是杀害棒球男孩的凶手,罗西感应到她后,连续两次企图抓住她,但均被她压倒。
此外,她还感应到了盒子丹,并和丹成了灵魂忘年交,两人联手找寻帽子罗西一伙。
ABC汇入D:高潮在图书馆阿布拉的强大助攻下,盒子丹成功找到帽子罗西一伙,用枪杀死了帽子罗西以外的凶徒(故事设定:帽子罗西一伙吸食年幼闪灵者的气连结一体,母体在帽子罗西,可以青春永驻长生不老,但无法抵抗外力伤害)。
由于帽子罗西难以对付,为了永绝后患,丹和阿布拉想到一个办法,两人回到闪灵酒店,守株待兔、等待罗西(故事设定:对于丹感到可怕的地方,同样适用于帽子罗西)。
闪灵酒店的三个人对弈剧情个人认为很精彩,这里致敬了《闪灵》很多地方,就不剧透了。
9 ) 没看过闪灵但很喜欢这部
我很喜欢,可能因为我没有看过闪电吧。
虽然知道闪灵很好,但我其实是对一些灵异鬼怪有点害怕的人,所以一直没有看闪灵,担心对我来说太恐怖。
这部片子好像是闪灵的续作,shining这个概念贯穿其中,但其实并不完全是闪灵的续作。
虽然男主以及酒店的线索是贯穿在影片里边的,但男主说的Shining,在小女主那里却是major魔法,所以这其实是两部有点不同气质的电影。
我感觉这部电影在同类型的驱魔通灵或是惊悚恐怖类里面算是很不错的,完全度很高,bug基本上也比较少,也没有那种人物很蠢的来推动剧情进展。
整个故事的逻辑还是很通畅的,节奏也流畅。
基本没有枯燥或是太过乏味的部分,情节的推动也挺好的,小故事的设置也不错。
人物的成长也有。
影片里面有三种不同的人,面对通灵不同的态度。
酒店的鬼魂以及反派团队的态度则是应该利用通灵的特质,更应该吸收其他通灵人类的灵气来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获得的青春可长生。
反派中的小女孩的被吸收过程也蛮有特色,他一开始是以私行的正义出现,然后就被反派女的美貌及魅力所蛊惑,加入了残害其他通灵人类的行列。
男主小时候被闪灵酒店所骚扰留下了不小的心理,认为应该把自己闪灵的特此隐藏起来。
小女主是大胆的展示自己的通灵能量,尽管途中经过了恐怖被惊吓,被追逐,依然觉得正面迎击才是最好的。
的确,正面迎击才是最好的,片尾的点题也很好。
男主跟小女主的父亲虽然上升,但以灵魂的形式闪现也算是给予影片正面的能量。
影片有些地方其实还挺有趣的,甚至有时有点诗意的气质,比如开篇反派女引诱小女孩的过程,比如反派自己历数他们经历了多少时代的变迁,见识多少历史人物的进程。
反派的口号也挺有意思。
eat well , stay young ,live long.长生并不是完美的,要结合青春永驻以及生活美好。
很多幻想作品在设定长生时,其实忽略了其他附带条件。
10 ) 剧作崩盘的《睡梦医生》
还没看原著,所有观点仅针对电影。
在某些意义上,是一部合格的电影,至少看起来像是要赚钱的架子。
从不同角度复盘一下剧作。
《闪灵》中,主要叙事空间是酒店,主要人物关系是BMW。
出现的鬼魂,灵异功能,都是在人物关系背景下生效。
比如父亲的欲望-出轨-老女鬼,男孩的孤单-到处逛-双胞胎女鬼。
在人物关系困境下,鬼魂的存在暴露了人的内心世界,这是最恐怖的事情。
再看《睡梦医生》,男主除了纠葛多年的老黑人,并没有固定的人物关系。
男主的童年痛苦-女鬼-盒子。
这个线和后面出现的黑人小女孩,以及反派女人都不产生情感联系,挺失败的。
而且,老女鬼在《闪灵》中是父亲碰到的鬼魂,现在反复出现在男主的世界,好像除了是鬼对接不上其他的欲望,莫不成他和父亲一起爱上了这个鬼魂?
来一个父子同妻的关系?
总之就是太弱。
其他几条线更是弱智的可怕,强加了灵气吸收的设定,出现了无恶不作的反派,以及天生超能力的黑人小女孩。
感觉故事是拼出来的。
最后绕了一大圈,终于回到酒店,要靠男主的童年饿鬼来战胜对手。
缺少内心斗争和人物转变。
烂多一句,直观的感受像是幼稚又自恋的成长故事,我天生就是拥有超能力的人,生来只为打败坏人美术。
本质还是聊剧作。
从空间上看,这部片子非常多的外景让设定特别容易崩盘,古老的吸收灵气设定,强行用台词解释和现代环境的融合问题。
我的观点是环境需要的不是合理,而是和人物内心世界产生联系。
《闪灵》中,家人们在进入酒店前基本是内景,不展露过多的社会环境,是保护整个片子的设定,保护观众的沉浸感。
除了喜剧,谁会相信白天大街上有鬼呢(回魂夜摸胸)。
空间基本是日常的场景,除了最后的酒店。
最远也就是树林和废弃工厂了吧。
缺少象征性的主叙事空间。
比如反派有一个基地,就在精神病院地下之类的。
我真不懂为什么设定反派是开车队到处跑的,这个空间糟糕的啊,一点氛围都没有。
树林、黑人女孩家、男人小时候的家、男主的租房,各个空间都陈设的非常丰富,但少见和人物内心状态结合的置景,甚至置景抢戏,大于主角/干扰情绪。
这就是广告行业对电影的冲击吧哈哈哈哈,只会在乎景深层次和灯光层次,而不会阅读剧本形成判断的打工人,打几个伦勃朗光就高潮的艺术家。
视听。
反复对照两个片子,就会发现库布里克和普通导演之间存在的鸿沟。
语言,是由一个个字组成的,视听语言能叫语言,就是一个个字组成的,有逻辑排列的体系。
而不仅是强烈的构图,前后景的人物关系,观众不是点读机,观众需要感受。
忘了第几场戏,频繁的出现过肩关系镜头,我就知道完了。
不成体系。
表演得有多费劲啊,基本上除了打斗和超能力,太多没有动作的,煽情的台词。
肉眼可见的紧绷表演。
看着都累。
好电影还是少,好生意也还是少。
整体下来,带入感很差。
可能是主角行动线不明确,是被动的接受反派的追捕。
可能是主角的内心欲望不明确,是童年阴影还是在学校和家庭中被当成异类?
可能是主角不明确,我他妈看哪个都不像是主角。
反派像,欲望是小孩的灵气,困境是性别和人种。
男人,黑人女孩,同伴,社会环境都是她的阻碍,她一步步突破,最后见到了更饥渴的魔鬼,死在了和自己同样欲望的饿鬼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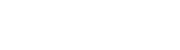





















































成也闪灵,败也闪灵,喜欢里面再现闪灵的场景同时,也因为演员换了带来了不适,去掉闪灵光环,剩下的是个世界观完整,两拨非人灵力乱战的奇幻片,较为平庸。不过这部片真是破除童年阴影的神作,把小时候害怕的妖魔鬼怪变成了口袋妖精。另外,伊万的演技和颜值真是除去闪灵彩蛋外最大的亮点,他所扮演的沉睡医生太符合了,有他这样帅气温柔的人临终送行,谁不会成佛呀。
豆瓣对续集和恐怖片太不友好了,并没有那么差。
故事讲得蛮清楚的,也很忠于闪灵电影,但缺点也是太一板一眼致敬/模仿/重现闪灵了,把所有元素都依葫芦画瓢堆砌了一遍,以至于看到后面高潮变成疲劳。酒吧谈心那一段依然差一口气,只有男性视角就是不行。。。这里面母亲角色的描绘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音效太猛了啊啊啊,心扑通扑通的
一流恐怖片的三流惊悚片表亲,就回忆杀还能提提劲。浴缸里的老女人好可怜。6
不挂闪灵续集的话 就是个超能力故事 沾上闪灵只给我看这个的话绝对给你不及格。
为啥时隔一阵还涨分了
没《闪灵》做参照,它还算过得去;有了《闪灵》作参照,它索然无味;如果把它当成《闪灵》的续集来看,它是狗尾续貂。
超长的超能英雄大戏,好过dc作品
shining被具象化之后,整个故事就变成了《闪灵2:变种人决战摄魂怪》
主线展开之后挺有趣挺精彩的,虽然不喜欢《闪灵》但还是看得挺开心。(毕竟是用信用卡公司送的免费票看的) 不过没看过前篇的男朋友表示卧槽2个小时四十分钟就是受刑hhhhh
啰里八嗦腻腻歪歪的,情绪已经无法被氛围笼罩,变成了隔岸观火的两个半小时的煎熬过程。
我不喜欢闪灵,所以没有情怀作祟,单独看这个电影,真的很难看!
那些说狗续貂尾的,是看过多少次闪灵🙄🙄🙄🙄🙄
这小女孩简直是闪灵超人,感觉比x教授和黑凤凰合体都强,好奇为啥结尾打女boss要跑,这能力完全不虚啊,这电影可以说是一个命题作文,以闪灵背景制作一个超级英雄电影,最好看是小女孩埋伏女巫那段,可全片这种闪灵对决太少了,谁想看你打枪战啊,雪山高空镜头拍车去酒店加上经典配乐真的沉浸回去了,但也只有这一段,180分钟被闪灵束缚太严重了,整个观感就像女巫看到电梯出现的红酒一样,若无其事的走了
吸氧吸了两个半小时都没有一个237吓人…
(5.5/10)导演剪辑版。睡梦罗汉拳都比这个睡梦医生好看多了。回到酒店之前虽然愈发沦为俗套的超能力者打怪,但风格至少统一。硬套上电影闪灵不知道有何意义,闪灵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归功于电影空间的塑造,这片离开了那个location或者说突破了那个space,就需要发展另一种拍摄手法了。。三小时不算短,看看老马丁的三小时效率多高?就颁奖后群聊那场戏是有多充分。看到有老金的书迷争辩说这部更贴近小说原著,库布里克当初才是魔改,但咱看的不就是电影吗?提小说干嘛。
前面就像裹脚布,又臭又长,就拍后面一小时足以
鬼故事突然变成枪战片,问你怕妹:)
哈哈哈前面看得我一脸懵逼,后面津津有味,千万别烧旅馆呀哈哈哈